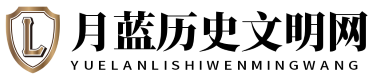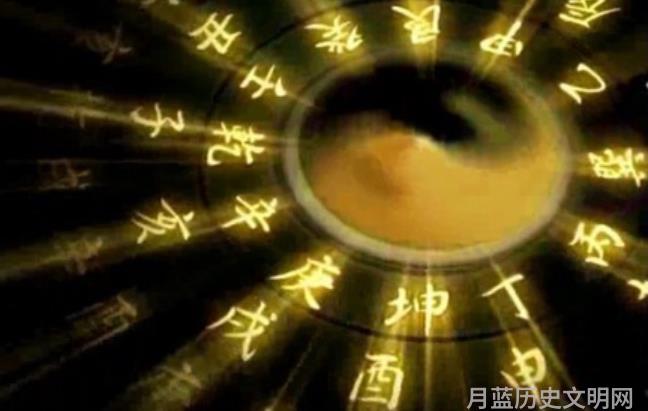前南斯拉夫解体原因中央权力过度集中导致政治改革失败

曾经,大南斯拉夫是一片改革开放的热土,市场体制完备,经济繁荣,人民生活水平高昂。与世界和平相处了45年,然而在1991年,它却瞬间分崩离析,瓦解成五段,“残扇无骨”。之后,由塞尔维亚和黑山组成的小南斯拉夫,在国际制裁的艰苦情况下艰难度日,更遭受了以美国为首的北约78天的狂轰滥炸,痛苦重重,困苦不堪。难以置信的英雄主义和数不清的人民苦难,最终化为悲剧性的结局。是国家遭遇各种不幸的总根源,是由于民族利益冲突的无休止的出现。
大南斯拉夫有超过二十个民族,其内部六大民族都拥有自己的共和国。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该国家的兴衰都与人民的命运密不可分,更多的是深刻反映着族群之间利益的冲突,是无数次不可避免的人与人之间无止境的矛盾。
说唱的形式再次印证了民族关系对国家发展的重要性。它就像洗衣盆里的墨水一样,将盆中所有的衣服都染上它的颜色。
纵览前南斯拉夫历史,我们可以看到以下主要特点:首先,从建国到解体期间,民族之间的冲突一直持续不断,即使在铁托统治时期,民族矛盾也时有暗流涌动。其次,民族之间的冲突往往显得非常激烈和残酷,在二战前,克罗地亚曾暗杀国王,塞族也曾暗杀克罗地亚议员,而在二战期间,170万南斯拉夫人中,很大一部分是克塞两族相互残杀的结果。再次,在90年代南斯拉夫多地的冲突和战争中,死伤人数高达百万,仅在波黑战争中,便有20万以上的人失去了生命。最后,民族斗争主要集中在塞族和其他民族之间,特别是与克族之间的冲突更为显著,在这种斗争中,塞族往往面对其他民族的明暗支持,例如,在科索沃的阿族反塞斗争中,其他各族都曾在不同程度上给予了其支援。
尽管在解放的实践中,铁托推行了大小民族平等和团结友爱的政策,他也是非结盟运动的旗手之一,然而,在寻找更为有效的解决方案这一方面,一直没有找到切实可行的办法。这种适合南国说唱格式的演绎形式,再次喊起了人们对民族关系的重视,它始终将在世界历史中占据一席重要的位置。
曾经的内外政策让这个国家繁荣稳定了二、三十年,但它最终陷入了“按下葫芦浮起瓢”式的循环之中,难以自拔。在这个国家统治者去世后不到十年的时间里,民族仇杀的烈火将一个毫无问题的社会主义国家化为乌有。
接下来,我将介绍我所经历过的一些情况。
夭折的改革
在80年代,南斯拉夫的经验备受我国内部关注。就在这个时候,南斯拉夫的经济开始日趋恶化,这引起了学术界和领导层的思考。1988年,我作为大使前往南斯拉夫,部长交代我要弄清楚这位实施改革政策最早的社会主义国家为何会陷入如此困境,因为中央领导层非常关心这个问题。在南斯拉夫期间,我在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和波黑三个共和国进行了调研,与中央和地方的许多专家进行了交流。最终的结果表明,问题主要出在各个共和国之间,并具有以下实质。南斯拉夫早期实行社会自治制度和协商经济体制,曾经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但后来,随着联邦当局权力的节节下放,各个共和国和民族便开始打着加强“自治”和“协商”的旗号,相互之间争权夺利,与联邦政府纵向对立。结果,联邦政府的大权旁落,各个共和国的权力却不断扩张,同时民族主义也不断膨胀。这样导致了多个分散而平行的经济和权力中心的出现。
当各个共和国和民族当局掌握了大权之后,并没有认真贯彻社会自治和经济协商制度,而是实行了官僚集团的集中领导。企业和社会团体的代表大会和选举产生等制度虽然进行,但均是有名无实的,生产计划仍由共和国政府统一下达,企业和团体的领导也都由他们委派。在这个过程中,政企合一,权力并未下放。因此,南斯拉夫的经济改革在中途夭折了。这主要是由于各个自治省并没有实行国家的改革措施,而是截取了联邦下放的权力,形成了“中梗阻”之症。我深刻认识到这一问题在南斯拉夫的尖锐性。
使馆向国内汇报此事后,得到的回复是部长的问题已经基本得到解决。
南斯拉夫,一个陌生而美丽的国度,却深陷着科索沃问题的泥潭,让人不禁心疼。当我踏上这片土地时,就被无休止的全民集会和悲愤的演说所深深震撼。在贝尔格莱德和塞尔维亚城镇,更是出现了大规模的集会和争吵,一片混乱。封闭的联邦议会大厦里,塞族群众的冲突和争吵不断,让人倍感无力。初来乍到,我感到被这样的局势所困扰和迷茫,但是在同志们的帮助下,我慢慢理清了思路。
铁托时期的民族政策主要是反对各民族的民族主义,特别是遏制大塞尔维亚主义的势头。其中,最具有标志性的措施便是在塞尔维亚境内建立了科索沃和伏依伏丁纳两个自治省,并赋予他们和共和国基本同等的权力,以安抚阿尔巴尼亚和匈牙利等少数民族的民族主义者。虽然这一措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民族问题的矛盾,但塞族仍然不能忍受境内的阿尔巴尼亚族同自己平起平坐,这早已成为了塞族的痛楚。对于铁托,有人心怀不满,传闻他在塞尔维亚的胸膛上扎了两刀。但是大塞尔维亚民族主义却没有被削弱,反而被压制和压抑,如同一股憋足了劲的力量。当铁托去世后,这种力量便在1986年得到了塞尔维亚政治家米洛舍维奇的历史性代表。另一方面,阿尔巴尼亚族民族主义同样在发酵,他们不满足于自治省的地位,而是要求脱离塞尔维亚建立独立共和国,甚至有些极端分子提出要与阿尔巴尼亚合并的口号。这就是1988年紧张局势的形成背景。
塞尔维亚当局处理科索沃问题的方针十分强硬,不愿对话、不愿分清事实、不愿劝导。他们将所有事件定义为反政府行动,宣布紧急状态,大量派遣军警,逮捕科索沃自治省的阿尔巴尼亚族和为首者,即使是那些不支持科索沃独立的全国和温和派人士也难逃其咎。最终,塞族人士组成新的领导班子,这些措施让科索沃更加深陷于被压制的窘境之中。
1989年初,塞尔维亚议会通过宪法修正案,收回了科索沃自治省的外交、国防、内务、司法、计划等所有大权,只留下了自治省的名义。科索沃被压得无法透过气。
阿尔巴尼亚族的独立运动始终没有停止,只是转入了地下。被解散的议会秘密召开会议,在1991年成立了“科索沃共和国”,但这个共和国被塞尔维亚当局视为非法。自此,阿尔巴尼亚族在塞尔维亚的一切活动都遭到限制,包括议会选举。极端分子开始采取武装斗争,建立了“解放军”,带来了不断升级的武力冲突。在针对武斗分子的打击中,塞尔维亚军警也误伤了许多阿尔巴尼亚平民。十年的时间过去了,科索沃的局势一直没有得到缓解。
曾经,美国领导的北约发起了对科索沃的战争,南联盟进行了英勇的抵抗。尽管他们勇敢地抵抗,但是由于力量悬殊,塞尔维亚付出了难以弥补的代价,而科索沃也从此消失在塞尔维亚的版图之外。
在前南,经济利益的冲突引发了危机,这种危机于80年代和90年代交替出现,一度推动前南走到了十字路口:走向统一或者以邦联形式维持国家的统一。尽管当时危机严重,但是维护统一的因素仍然占据主导地位。因为这符合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所以前南没有分裂。然而,这一局面在后来发生了变化,引起了新一轮的危机。
前南与其他东欧国家不同,是一个不结盟的国家,无论是西方还是东方,在国际上反对南斯拉夫是主流。保持南部联盟的统一对于巴尔干和整个欧洲的稳定都至关重要。
当时的情况是,尽管北方的共和国(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也有要求独立的呼声,但是他们真实的目的是想压制联邦当局接受他们的更多要求。主张分离的极端分子力量有限,联邦政府提出了新的经济改革纲领,核心思想是推行“彻底的市场经济”,按照市场原则协调各共和国之间的关系,逐步实现私有化,将加入欧洲经济一体化定为努力的目标。大多数共和国都赞同这个纲领。此外,南斯拉夫的各个民族自本世纪初以来一直生活在一个国家里,建立了全面的联系,经济关系密切,混合家庭也屡见不鲜。各族人民都希望继续和平、稳定地共同生活。在国际上,除德国外,所有欧洲大国和美国都明确反对南斯拉夫分裂,以保持巴尔干的稳定,并防止德国从中谋取利益。
这段时间里,我们与许多权威人士讨论了南斯拉夫的形势,其中包括著名经济学教授格里戈罗夫(现马其顿总统)、外交官和图季曼等人。格里戈罗夫认为,南斯拉夫各共和国之间的经济联系是决定性因素。由于现在有一个被大家所接受的改革纲领,因此南斯拉夫分裂的可能性并不大。1990年底,克罗地亚总统图季曼在会见我的时候说,南斯拉夫不会从世界地图上消失,但它存在的形式将会发生改变(克罗地亚主张邦联制)。
最有趣的是同美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齐默曼的一次谈话。他告诉我,在南斯拉夫问题上美国和中国的立场是一致的。尽管美国有些朋友可能想从南斯拉夫局势中谋取好处,但这是危险的。南斯拉夫内部正在出现好的变化趋势(即新的经济改革政策和自由化),没有理由不让它继续发展。正在这时,齐默曼接了一个来自萨格勒布(克罗地亚首都)的电话,我听到他高声说道:“告诉他们,美国反对南斯拉夫分裂,美国不会支持他们的行动,告诉他们,这是华盛顿的立场,而不是齐默曼个人的立场。”放下电话后,齐默曼对我说,这是他的一位去克罗地亚出差的同事打来的电话。话音刚落,一位南通社的记者恰好在场,他听完齐默曼的电话后马上告别离开。当晚,该社发了一则新闻,导语是“美国反对南斯拉夫”,第二天,南斯拉夫各大报都以此为头条,报道了美国大使的这次谈话。
无论是国内还是国际,“前南斯拉夫解体”本来是可以避免的。但是由于南共盟的衰落和联邦政权式微,该国已经失去了运转的轴心,命运掌握在相互攻讦和倾轧的各个共和国手中,特别是塞尔维亚和北方两个共和国。
在前南斯拉夫的2340万人口中,塞族占了37%。他们在上世纪初的巴尔干战争和二战期间的反法西斯战争中立下过赫赫战功,一直以来都自称为老大。早在王国时期,他们就提出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国王”的大塞尔维亚主义口号。其他民族的民族主义也很强烈,特别是人口较多的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而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有天主教文化背景,塞族人则有东正教文化背景,两者始终不和。由于他们之间的冲突不断升级,最终导致了前南斯拉夫的解体。前南斯拉夫的解体是由于各共和国之间的国体之争引发的灾难性结果。
北方的共和国认为大塞民族主义对他们构成了威胁,为了应对这种威胁,他们坚决主张改变联邦制为邦联制。与此相反,塞尔维亚的政策是依靠联邦制度来维护自身利益,同时反对邦联化。他们表示不希望留在联邦中的共和国可以自行决定,但所有的塞族居民都必须留在原地,因为他们都应该“生活在同一个国家内”。不过,其他共和国认为,塞尔维亚坚持的联邦制度是以他们为中心的高度集中制度,而所有塞族居民生活在“同一个国家内”的口号,则意味着塞尔维亚想要占领克罗地亚1/4面积的土地,以及占领波黑一半面积的土地,这是其他共和国绝对不能容忍的。
这场激烈的国体之争导致灾难性的后果:首先,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波黑和马其顿相继宣布独立,加剧了他们之间的分离倾向;在克罗地亚,由于与塞尔维亚之间的大规模战争,塞尔维亚曾一度占领该国领土的1/3,导致了克问题的国际化,最终塞尔维亚被迫撤出;而波黑爆发了更大规模的战争,穆斯林、塞尔维亚和克罗地亚的三大族群相互混战,争夺Control of the land。南斯拉夫的解体是一段令人痛心的历史。在这场历史上的实践中,南斯拉夫的历程再次证明了列宁名言中所承载的深刻内涵。
南斯拉夫的历史是非常复杂的,这个国家一直面临着严峻的问题。尤其对于南共和国的领导者铁托来说,如何解决各民族之间的矛盾成为了立国之本。在其任期内,南斯拉夫的疆域得到了巩固,国家走上了繁荣快速发展的道路。
南斯拉夫的实践已经证明了正确的解决方法是实行“民族平等”、“社会自治”,并采用联邦制。由于这个国家民族多元,六个主要民族的大小并不悬殊,互相间的历史、文化差异和疆界也很明确。因此,铁托时代实行的政策,可以很好地解决各民族之间的矛盾问题。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局势发生了逆转。前南斯拉夫的解体成为了令人痛心的历史事件。在这一过程中,南斯拉夫六个民族之间的历史和文化差异不断激化,各民族之间的关系日益紧张。由于塞族在这次分裂中一度占据上风,塞族也进行了民族清洗并占领了大片领土。最终,在北约的介入下,南斯拉夫签署了代顿协议,波黑的领土得以保持完整。而1992年初,塞尔维亚和黑山两个共和国又建立了新的南斯拉夫联盟。这一场解体没有给南斯拉夫带来任何好处,反而造成了成千上万人的伤亡和流离失所,经济也受到了长达数十年的打击,使得巴尔干地区落入到漫长的动荡时期。于一个真正符合国情的民族政策的正确性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随意超越其合理的界限。前南斯拉夫的解体无疑宣告了其民族政策的失败。尽管可以列出各种原因,包括国际背景等,但恐怕其症结是上述辩证法的规律不幸而应验。
在建国初期,为了实行“民族平等”、“社会自治”,我们非常尊重各民族的历史、文化、宗教、语言,并大力发展他们的经济,不搞过多集中,而是让各民族拥有名副其实的自治,让人民多些权利。这些政策都在前南斯拉夫的建国初期得到了出色的贯彻,同时也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然而,到了70年代,情况开始发生变化。晚年的铁托领导下,面对各民族主义的压力,他开始一味迁就退让。1971年,通过的宪法修正案规定,联邦的大部分权力下放给了各共和国。随着时间的推移,1974年通过了新宪法,剩下的行政和经济管理等大权也全部下放。从此,各共和国、自治省也就变成了一国之内的“国中之国”。
南斯拉夫率先抛弃了苏联模式,选择了自己的发展道路。但是,如果在实行民族政策时超越了合理界限,一味迁就各民族主义的压力,那么成功的道路也会成为失败的通道。南斯拉夫的历史告诉我们,唯有充分尊重各民族的历史、文化、宗教、语言,让各民族享有名实相副的自治,才能让国家实现长治久安,人民生活安居乐业。前南斯拉夫从极度集中的一端走到了极度分散的另一端,把那些保证国家统一的不可或缺权力也都下放给了地方,为国家的解体创造了条件,这是我们最为惨痛的教训。
南斯拉夫的解体始于南共盟的开始。该党为了体现党政分离,已经放弃了对社会的领导作用,改行指导作用。在1990年召开的十四大上,我身在来宾席上亲眼目睹了该党内部的分裂。斯洛文尼亚代表率先离席离开,各共和国共盟之间再也没有找到弥补分歧的办法。大会提出反对包括自己在内的任何政党的垄断,并肯定了制度化。在随后的各共和国进行的自由选举中,原南共盟策划的反对派盟纷纷取得了胜利,成为新的执政党。取消党的领导作用,国家丧失了维护统一的核心,这是前南斯拉夫留下的另一个严重的教训。
南斯拉夫是在不同的历史阶段走了各自不同的道路。但从南斯拉夫的解体中可以看到,一个国家的统一需要具备统一的核心和明确的权力界限。这是维护一个国家和解决国内矛盾的基石。如果我们超越合理的界限一味地追求权力下放,那么就会把国家的统一危险的推向解体的边缘。我们应时刻谨记南斯拉夫的教训,警醒自己,维护国家的统一永远是我们的重要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