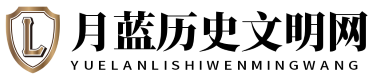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理论与史学研究中心
作者:陈峰 原创发表:《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3期
中国现代史学的一个显着特点是追随西学。 兰克经验史学的传入和流行,掀起了史料研究的潮流,塑造了民国时期占据主流的史料学派。 西方汉学特别是欧洲正统汉学的归纳和论证,导致中国历史研究的领域、材料和方法发生了重大调整。 西学本身的转型、美国“新史学”的出现、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兴起、美国国学的出现,也孕育和推动了中国历史的不断转型。
中国传统史学原本是一个自给自足的体系,但近代以来其根基已经动摇。 其显着特点是顺应西学潮流。 根据当代人的观察,因为“近代科学的发展和资本主义的进步已经将整个地球融为一体,无论愿意与否,中国现在已经成为世界的一部分”。 “随势而动”是指“中国学术思想的转移正是随着世界学术潮流的转变而发生的”。 ① 后世学术史家也说:一切新历史流派“都是在西学浪潮的冲击下诞生的,或以外国为师,或以外国为鉴……或依托外国人要尊重自己。” ②西学对民国史的影响可分为西学史学和西学汉学两部分,下文分别论述。
一、兰克经验史学与中国史学的融合
首先引起中国史学近代变化的是欧洲和日本文明史。 20世纪初,梁启超等人掀起的“新史学”思潮或“历史革命”,是西方文明史学在中国的回响。 梁启超以日本历史为中介,引进西方思想资源。 19世纪后二三十年,日本民间学者流行的是“文明史”,其根源就是以基佐、巴克尔、斯宾塞为代表的启蒙史学。 ③早期留日的中国人受其影响较大。 1902年,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向中国读者推荐基佐的《欧洲文明史》的日译本。 ④梁启超这一时期的历史思想明显带有文明历史的痕迹。 他尊重人民的历史、排斥君主的历史的思想直接受到了文明历史的启发。
但民国以来,“新史学”退潮,西方文明史的影响逐渐衰落,取而代之的是兰克经验史。 事实上,兰克的经验史学在欧美已经开始衰落,但其残存的遗产却在五四运动之后的中国产生了主导性的影响。 王荣祖在讨论兰克史学与中国历史的关系时说:“兰克著作有五十多部,几乎没有一本被译成中文。他的史学虽然没有真正传入中国,但他所倡导的史学方法却进入了中国。”贝海姆等人的著作中的中国,比如姚从吾从北大到台大教授兰克的方法论,杜惟云在清华大学对梁启超教授的中国历史研究方法的研究也基本遵循了同样的路径。章太炎在写《送别清朝开国实录》时,也批判性地使用了原始史料,可以说也是受此影响。至于其他像王国维的“双证法”,陈尹科留学西欧,受到兰克学风的影响,更不用说受到发起怀疑古风的顾颉刚的影响了。 鉴于传说的不可靠性,可信的历史必须根据可靠的史料来重建,而孟森则利用记载等原始材料来验证清史事实。 可以说,他直接或间接地受到了兰克史学方法的影响或启发。
兰克史学方法的核心是史料的批判性运用,因此史料问题就成为最基本、最重要的问题。 认识论的客观主义是兰克历史学的另一大特点。 只有具备这两个基本点,历史才能成为科学。 兰克对中国史学的影响最集中地体现在傅斯年身上。 傅斯年在欧洲留学时,受到兰克经验史学的洗礼,表现出极其重视史料的倾向。 他很欣赏兰克和蒙森,曾说过:“这纯粹是根据史料来探究史实。在中国,这绝对是司马光乃至钱大辛治史的方法。在西方,这也是著名的史实。” Ruanke 和 Momsen 建立的方法。” 点。” ⑥据历史语言研究所人士后来回忆,傅斯年回国时曾宣称“我们是中国的兰克学派”⑦。
傅斯年特别强调史料的中心地位。 他在《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工作宗旨》中宣称:“现代史就是研究史料”“只要把史料整理一下,事实自然就清楚了”。每一点材料都会产出一个好产品,每十分之一的材料都会产出“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产品,没有材料就不会发货……他可以看到材料中的一切,他不会”材料之外,切不可过分。” ⑧后来,他反复强调:“历史的对象是史料,而不是文字,不是伦理学,不是神学,也不是社会学。 历史的工作是整理史料,不是建构艺术,不是澄清事实,不是支持或推翻这个运动或那个主义。”[9]尽管傅斯年的历史宣言不乏令人震惊的成分,但总的来说,它仍然是表达了他的历史观点。
痴迷于使历史科学化的傅斯年也信奉客观主义。 他在《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工作宗旨》中宣称,要把历史学建成“与自然科学同等水平的事业”,把历史学打造成“客观历史学”和“科学东方学”。 ” 他这样总结中国和欧洲的历史观:“第一,历史观的进步在于从主观哲学和伦理价值论向客观史料的转变。 第二,历史书写事业的进步在于人文手段的运用。 它可以变成生物学、地质学等一般性的事业。” ⑩他坚信,只要消除历史记录所附加的道德意义,历史的客观性就可以通过每一条“赤裸裸的史料”来展现。 因此,他认为:“我们决不能把我们主观的价值论放进去……我们既不能依赖传统的权威,也不能追随继承的品味。” (11)他主持创办历史语言研究所的道路,“意为兰克大师的旧智慧”(12)。 可以说,历史语言研究所是兰克史学的中国版。
事实上,“新史学”的先驱梁启超早已间接受到兰克的影响。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梁启超赴法国学习两位法国历史学家查理五世·朗格卢瓦和查尔斯·塞尼诺博斯与德国历史学家恩斯特·伯恩海姆合着的《史学原理》。 “历史方法论”的影响。 比较梁氏的《中国史学研究方法》与《史学原理》,“我深感两者的联系极为密切,梁氏的突破性见解大多源于郎、色”。 (13)两位法国学者合着的《史学原理》强调历史文献和批评的重要性,基本呼应布伦汉的《史学方法论论文集》。 《布伦纳姆之书》是将兰克的史学还原为方法论的杰作。 (14)据此推论,从历史研究方法上看,梁启超实际上间接继承了兰克的衣钵。 兰克的历史学也借用了梁氏的“中国史学研究方法”,在中国学术界深入人心。
总之,民国时期以胡适、顾颉刚、傅斯年为代表的史料主流流派基本上是卜兰克派。 因此,经验史学成为1949年之前西方史学思想对中国影响最大的思潮。
2.受欧洲正统汉学启发的中国历史
汉学是广义上的历史学,可以说是西学影响中国历史的最重要途径。 1945年,顾颉刚在回顾和总结百年历史发展时说:“近来,欧美、日本学者对汉学研究作出了巨大贡献。 他们的成果传入中国,刺激了国内学者,使中国史学也随之进步。 他把民国史的成就概括为六个方面:“一、考古史前史研究,二、中外交往史及蒙古史研究,三、敦煌学研究,四、研究”关于小说、歌剧和通俗文学。” ,5.古代历史研究,6.社会历史研究。” (15)前三者都没有脱离欧洲汉学的影响。 可见,中国历史研究已成为世界性知识,西方学者发挥主导作用。
胡适在《中国研究季刊》刊物中坦言:“我们现在进行中国研究,必须打破孤立的态度,要有开放的心态进行比较研究。首先,在方法上,西方学者研究的方法古代研究已经影响了日本学术界,而我们还处于寻找冥界的时期,这个时候我们应该虚心地采用他们的科学方法来纠正我们无组织、系统的习惯。第二,在材料方面,有欧美日学术界的无数成果为我们提供了借鉴和比较,可以为我们开启无数新方法,为我们提供无数可供借鉴的镜子。学术最大的敌人是无知;无知的唯一良药就是收集供参考和比较的材料。” 基于这样的认识,胡适发起的“整理国遗”运动也与海外汉学相融合。 “整理国遗”实际上就是“按照受西方‘汉学’影响的西方‘汉学家’和日本‘中国学者’的研究方法和范围进行研究”(16)。
在国际汉学的冲击下,中国史至少发生了三个变化:一是研究领域集中于西北边疆历史地理和中外交往。 其次,史料的使用偏重正史以外的新材料,特别是考古资料和外国文献。 第三,研究方法采用文献学的方法来考证历史。 (17)
清末民国时期西北历史地理研究的蓬勃发展,与欧洲汉学重点关注东方特别是中亚的研究方向不谋而合。 民国历史大师的学术方向多与西北历史地理有关。 对西北边疆历史地理的研究在王国维的学术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并且始终绵延不绝。 1925年至1927年致力于蒙元史研究,撰写了《鞑靼考试》等多篇在国内外有较大影响的论文。 他的两本《西湖考》和一本《精曲考》都是伯希和写的。 写《西湖续考》的机会来自于阅读伯希和的就职演讲《东方古代文字学和史学的最新发明与结论》。 我了解到,西方人近年来在东方研究上取得了进步,他们的发明与古书是一致的。 陈元的宗教史研究也多与西北边疆历史地理、中外交往史交叉。 陈寅恪善于用“特殊宗族的著作”来证明“塞外的历史”。 这种对西北历史地理的研究,实际上是与西方汉学家对话的产物。
但当时国学泰斗章太炎并不认同这种倾向。 他把“考边塞而留内政”视为学术弊端:“今议汉史者,喜议其余支系,议元史者喜欢详细说一下奥罗斯印度,这两个都是过去常见的,今天是做不到的。从它的政治风格和教义来看,虽然过去是孤立的,但闲暇时考察一下也无妨。如果你只考察它的痕迹,而不了解它的内政和军事计划是如何导致这一点的,此外,当外国人读中国历史时,非中国人读的是它自己的历史。 (18)张的批评不无道理,这种习俗虽然有补缺、补缺的作用,但如果推到极致,难免会招致以婢女为妻的嫌疑。妻弃善去追求弱者。
桑冰指出,在欧美、日本汉学发展趋势的影响下,现代国学研究引起了学术风格和侧重点的变化。 其中之一就是材料的发现从注重文献转向注重实物和现场发掘调查。 (19)这一取向体现在陈寅恪对王国维“学术内容与治学方法”的概括中。 他认为“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 一是取得地上实物与纸上文字相互解释……二是取得异族古籍和我国古籍相互补充……三是取得外国书籍的概念与内在材料相互支撑。”(20)王国维、陈寅恪等高级历史学家的这种学术方法,也体现了西方汉学家在材料运用上的基本特征。
就连一向崇尚方法的胡适也认识到了物质材料的神奇功效。 他感叹道:“三百年的古韵研究,抵不上一个外国学者用活生生的方言进行实验,几千年的古代历史传说,抵不上三两个学者的实验。批评与批评。”河南发现龟甲兽骨,可以在实物的基础上建立古代殷商人的历史……学者们一直认为是纸上知识的东西,现在已经被从旧纸堆里扔了出来。 ……研究一下。” (21)在胡适看来,用科学方法处理书面材料只能达到考据,科学方法必须运用到科学材料(实物材料)上才能真正成为科学。
用考古资料补充历史、证明历史,是当时学术研究的新趋势。 新材料的开发和应用成为民国史学进步的主要推动力之一。 然而,对于考据派来说,“学习的唯一依据是新发现的材料”。 “有材料就有发现,有发现就会有文章。 建立学校的唯一途径就是寻找材料。” (22) 因此,新材料的使用就成为学术研究的最终捷径。 学者们对新材料的渴求,新历史的建构在很大程度上归结为新材料的发现和应用。 然而,仅仅使用新材料必然会导致对旧材料的异化和忽视。 正史是旧史料的代表。 民国学术界有“不读二十四史”的倾向。 (23)有评论家甚至认为“近代中国史学形成了史料丰富而史学贫乏的奇怪局面”。 (24)
语言学是欧洲正统汉学的基本功。 西方一些著名的汉学家,如查文、伯希和、高本翰、马伯乐、威廉·威廉等,都从中原、蒙古、西藏、中亚等地研究了历史、民俗、艺术等。语言学研究的视角。 欧洲汉学家的这条研究路径对中国学者有直接的启发。
傅斯年在欧洲留学期间,研究了西方比较语言学和语音学。 (25) 傅斯年回国后,在中山大学创办“语言史研究所”。 1928年,他又筹划在中央研究院设立“历史语言学研究所”,足见他对语言学的重视。 1936年,傅写了《性命古谚校正》,最终提出了“从语言学的角度解决思想史问题”的历史方法。
陈寅恪与德国语言批评有着很深的渊源。 在德国期间,除了在柏林大学研究生院跟随Heinrch Luders学习梵文和巴利文多年外,他还向FWK Muller学习古代中亚文字,向Erich Haenisck学习蒙古文字。 语言。 陈寅恪掌握多种语言工具,具备10多种语言的阅读能力。 他主张:“研究我国语言,必须研究与我国语言同科的其他方言,进行比较解释。 这是一条艰难的路。” (26) 1923年,他发现:“如果我们研究西方语言学,如果方法是汉藏文本的比较研究,其结果应该比干嘉和干嘉前辈的水平要高。”(27) )从1927年到1932年,陈寅恪对佛教经典和蒙古史料的研究基本上都是从比较语言学的方法开始的。陈寅恪对汉文考证的研究是世界上大多数学者所望尘莫及的。
因此,在民国学术界,历史语言学方法被视为成功的法宝和绝活,代表着尖端、前沿的研究,展现了治学的最高境界。 这种思潮无疑是对以语言学为基础的正统欧洲汉学的翻版。
三、西学之变与中国历史的新方向
20世纪上半叶,西方史学正处于从传统史学向新史学的过渡时期。 以兰克为代表的传统史学正面临危机。 针锋相对的批评和质疑正在欧洲和美国蔓延,一种新的史学正在逐渐形成。 达到顶峰的欧洲汉学并不是唯一在考证学派中表现出色的汉学。 它还孕育着变革的因素。 法国汉学大本营已分裂为以格拉尼安为首的社会学派,而主张以科学方法看待社会的美国中国研究也正在崛起。 西方史学的这种变革也促进了中国史学的发展。
20世纪20年代,美国的“新历史”开始传入中国并广泛传播。 鲁宾逊的《新史学》等著作一经问世,国内学者争相推荐,陶孟鹤、陈训慈、亨儒、谷逢池等人大力提倡(28)。 胡秋园认为,“新史学仍在前进,将在这里开辟道路,前景十分广阔”。 (29)黄文山认为近代史的潮流是新史学,这一运动已从萌芽发展成为盛大现象。 Lampley、德国Hit、法国贝尔和英国马尔文都对这一运动做出了贡献。 美国的《鲁宾逊漂流记》受生物进化论的影响,“注重历史过程的意义,主张动态的历史创造,他的弟子巴恩斯继承并发扬了旧作”。 (30)随后,巴恩斯(本茨)的《历史科学》、《新历史与社会科学》等“新历史”学派的著作陆续推出中文译本,其他未译著作也广为流传“新史学”派的主张已成为国内许多人讨论历史理论问题的依据,并体现在民国时期出现的一批《史学概论》著作中。中国,如卢绍基的《史学概要》、吴观音的《历史的阶梯》、李泽纲的《史学通论》、杨洪烈的《史地新论》和《史学通论》、卢茂德的《史学通论》。 《史学方法纲要》、周嵘的《史学通论》、胡哲甫的《史学概论》等,报刊杂志上发表的大量史学理论和方法论文,也吸收了“新史学”的思想。学校”不同程度。 然而,美国“新史学”的引进基本停留在观念层面和历史教育,未能深入到实际的学术研究,形成名副其实的流派。
20世纪30年代,马克思主义在国际学术界的地位迅速上升。 此前,马克思主义一直受到西方学术界的排斥和敌视。 然而,1929-1930年的世界大萧条和资本主义社会的深刻危机扭转了这一局面,马克思的历史判断此时得到了证实。 “1929年的大萧条结束了对马克思主义的漠视或蔑视时期。1930年以后,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广泛扩大,甚至那些拒绝马克思主义历史解释的历史学家也不得不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重新考虑自己的观点。” (31)
马克思主义和唯物史观作为一种西方学术理论,对中国史学的发展产生了深刻而巨大的影响,引起了中国史学的又一次方向性转向。 唯物史观引入中国史学,为社会历史的演变提供了一套新的解释机制,建立了新的历史体系,从而改变了历史书写的模式。 传统史学在阐释历史时,往往着眼于道德人心的变化和政绩的成败; 唯物史观则从经济角度出发,揭示人类历史发展变化的深层次动因。 传统史学往往采用划时代的叙述方式,缺乏内在关联; 历史唯物主义以生产方式的演变为线索,把社会历史视为一个有机体,构建了全新的历史过程理论。 同时,实证史料派注重史料的考察和整理,缺乏历史观或历史解释的成果。 由此看来,唯物史观指导下的历史学在中国学术的现代转型中占有关键地位,其对后来学术发展的塑造作用也不容低估。 但我们不应忘记,唯物史学的形成是西学对中学影响的产物。 其实就是应用源自西方的理论学说来观察中国的历史进程和历史现象。 后来唯物史观发展过程中暴露出来的各种问题,也与中西学难以协调一致密切相关。
唯物史学也与国际汉学有关。 然而,追求同样目标的并不是当时的正统汉学,而是法国格拉尼安学派等被孤立和批评的边缘学派。 郭沫若得知汉学家格拉扬(Granan)擅长用社会学的方法来对待历史,而且他的研究与他相似,但他没有机会看到他的作品。 (32)郭沫若的《甲骨文研究》和《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两书引起了法国汉学家马布尔的注意,他撰文评论(33)。 郭沫若写下《答马伯乐先生》予以回应。
最突出的是,唯物史观普遍引用苏联和日本的马克思主义汉学家。 大革命失败后,郭沫若流亡日本。 他以唯物史观为理论,以甲骨文、金文为资料,探索古代历史。 在此期间,他得到了田中庆太郎、石田干之助、梅原末治、原田周人、市村山次郎、古城贞吉等人。 、朱乔哲慈等辅佐(34)。 1931年郭沫若《甲骨文汇编》的完成,得益于日本友人的支持。 吕振羽对古代史的研究也广泛参考了日本汉学家的相关成果。 他的著作《史前时期的中国社会研究》被苏联和日本大多数历史学家公认为1933年后国际东方古代史的重大新创新,是新历史视角下唯一的中国原始社会研究著作。 “历史著作”。 他的《殷周中国社会》的成功,被认为“不是陆先生个人‘天才’的主观‘超验’结果,而是1935年新兴科学的时代和新水平的结果。”东方史》(35)。 简伯赞还不断介绍苏联汉学家在中国史研究领域的理论方法和实践成果,例如他对科瓦列夫《古代社会》的评论。 这充分反映了当时中、日、苏马克思主义学者对中国历史研究的融合趋势,并已织成一个大规模的学术交流网络。 特别是在中国社会史研究方面,中、苏、日三国学术界实现了高度融合。
由于对社会经济史的相似兴趣,历史唯物主义者也与一些美国华人学者有接触。 例如,陶希圣曾与哥伦比亚大学国际社会研究所所长卡尔·维特福格尔(Karl A. Wittfogel)合作。 陶希胜曾帮助维特夫收集信息,与他讨论问题,并将助手借给维特夫。 陶希圣弟子王玉泉曾参与维特夫太平洋调查资助的中国历史项目。 此外,陶氏的弟子鞠庆远、吴显庆、曾健等也受聘于威托夫从事社会经济史料的英文翻译和研究工作。 陶希圣主持的《食货》第五卷第三期也刊登了魏先生的文章《中国经济史的基础与阶段》,称赞他是这一领域的领军人物。
二战后,国际汉学发生了重大转折。 美国的汉学不断发展壮大,迅速取代法国汉学成为世界汉学的中心。 相应地,学术风格也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 传统的重视考古、文献研究的方式逐渐没落。 社会科学已成为汉学研究的主导趋势,从而超越了传统文史的局限性,涵盖了广泛的社会科学领域和世界。 汉学的发展从此进入了一个新的境界。 However, due to changes in international and domestic politics, academic dialogue and exchanges between China and foreign countries have been blocked for a long time, and Western Sinology has been unable to continue to play a guiding role in Chinese local historiography. It would have to wait until the 1980s and 1990s for Chinese historiography to be infiltrated by Western Sinology and stimulate its own sense of chan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