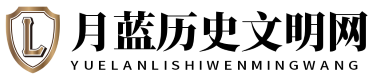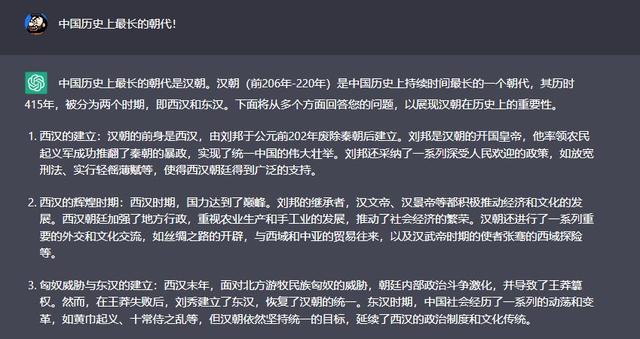马勇寻找中国近代转型的历史逻辑
马勇,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1956年出生于安徽濉溪,1983年毕业于安徽大学历史系,1986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历史系。着有《汉代春秋学研究》、《中国近代文化问题》、《超越革命与维新》、《中华文明通论》、《近代中国研究》、《新中国的背后》知识》:中国现代学者》和《晚清二十年》等书。
马勇在家中接受新京报记者采访。
马勇自1979年考入安徽大学历史系以来,已经在历史领域摸爬滚打了四十年。前年,他从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退休。 他以为自己即将开始舒适的晚年生活。 没想到,几所大学闻讯后,邀请他担任特聘教授或客座教授,社科院研究生院也重新聘用他为教授。 学生继续授课,他还受邀在一些音频平台开设中华文明通史、清朝历史等课程。
他的写作和出版从未停止过。 文章不时出现在报纸上,还有许多书籍手稿正在编写过程中。 今年10月,马勇的新书《现代中国的展开:以五四运动为基础》在五四运动百年之际出版。 它成为今年出版的为数不多的以五四为主题的专着之一。
在马勇看来,五四运动是继“殷周”、“周秦”之后中国历史上的第三次重大历史变革。 它是农业文明向工业社会过渡的重要节点。 这种连贯的历史视野是马勇区别于许多现代史学者的地方。 他的学术道路始于古代史,机缘巧合下进入近代史领域。 不过,这也让他的历史研究之路更加宽阔。
阅读心得:从煤矿工人到历史课
马勇1956年出生于安徽濉溪,因贫困,当地人自嘲为“安徽的西伯利亚”。 当他后来回忆起自己的求学之路时,他说,与同辈的都市人相比,他的童年、青少年乃至青年时期都是在迷茫中度过的,没有机会接触到很多书籍。
直到1979年考入安徽大学,他才从一个从部队回到家乡的煤炭工人转型成为一名知识分子。 当时的合肥,交通拥堵,就像一座孤岛。 安徽大学历史系刚刚成立,缺乏经验丰富的教师。 隔离的好处是人们可以安心学习。 大学四年,马勇从侯外录主编的五卷本《中国思想通史》开始,翻阅图书馆里能找到的思想史著作。
他把全部精力用于研究中国古代史料和《经史集》,四卷并重。 对于较难理解的著作,如《庄子·世篇》、《荀子·费十二子》、《说文解字》,以及从《史记》到《清史稿》的思想家传记》、《经济志》、《史老志》、《艺文志》等,他曾手抄一本,以加深理解和记忆。
扎实阅读原著经典,让他顺利考入复旦大学历史系,成为历史学家朱惟正的硕士生。 朱维正大师出身名门,是陈寅恪、钱玄同、孙冶让的弟子。 他是中国经学史、史学史、思想文化史、中西文化交流史领域的权威,在国内外享有很高的声誉。
马勇跟随朱惟正学习了三年,研究中国文化史。 从他的生活方式到他的研究兴趣和研究方法,都受到他的影响。 有熟悉的朋友开玩笑说:“连抽烟的方式都和朱老师一样。” 马勇很崇拜比他大二十岁的恩师,把他视为人生的榜样。 他所研究的许多课题也继承自朱惟正,如秦汉史、儒家史、章太炎思想、明清中西文化交流等。
马勇至今仍感激自己在朱惟正门下接受的专业历史训练。 这不仅开阔了他的视野,而且获得了治理历史的方法。 在计算机尚未普及的时代,历史学家需要复制大量卡片并做笔记以供随时参考。 不过,朱伟正要求学生不要抄卡片,需要的时候翻一下书本。 一遍一遍地重复,不仅可以加强对史料的熟悉,也是训练记忆力的好方法。
马勇在朱惟正的指导下完成了毕业论文《西汉研究》。 一向以尖锐直言不讳、当面批评人毫不留情着称的朱惟正对自己的爱徒大加赞赏。 后来这篇论文发表,朱惟正为其作序,说:“马庸的书力求超越现代和古代文学的传统争论,从从文化史的角度看……他勤奋踏实,没有一些青年学者的轻浮习气,说明他是一位有为的青年学者,在学习上有着顽强的毅力。
后来,马勇不负众望,在历史的道路上开辟了一片新天地。 他既继承又发扬了老师的思想,研究重点也悄然从古代史转向近代史。
近代史研究所:不以写作为追求,以学习为目的
马勇曾说过,他的很多人生选择都是被动的,包括工作单位和研究课题。
从复旦毕业后,朱伟正原本想让他有机会留在学校任教,但因人事问题未能如愿。 后来,他帮他找到了上海师范大学和上海社会科学院比较文化研究中心的工作,主任是王元华、黄万胜。 。 当时上海的单位招人特别困难。 一次偶然的机会,马勇到北京求学,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一待就是三十年。
马勇在求学期间致力于中国古代史特别是古代思想史的研究。 他相信老一辈学者“秦汉三代之后无学术”的说法,对近代史的研究较少。 20世纪80年代初的近代史研究确实没能摆脱“革命叙事”和“阶级分析”的传统。 学术受政治束缚、服务意识形态,不存在纯粹的学术。
马勇在《我的学术起点》一文中回忆说,当时“晚清史是前人花了不少功夫的领域,但与我当时更熟悉的古代史相比,当时,近代史的很多问题当时还不清楚,还没有人触及。由于时间原因和时代原因,总之,三十年前的中国近代史与古代历史相比,就像是未开垦的处女地。
俗话说“历史是胜利者书写的”。 尤其是在“政治主导”的环境下,对历代历史的解读不免受到诸多干扰。 马勇印象最深的是对资产阶级和洋务运动的重新评价。 随着思想解放思潮逐渐蔓延,流行了数十年的“革命叙事”悄然打开了裂痕。 那种政治保守、文化落伍的叙事方式逐渐被追求客观真实的历史叙事所取代。
研究者普遍认为,近代中国的历史进程中,除了政治革命和制度变迁之外,还有建设和发展的问题。 因此,对于改良主义、工业救市、科学救市等中国近代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负面事件,以及李鸿章、康有为、梁启超、胡适、傅斯年等有争议的人物,有更多的正面评价。 一些过去禁忌的话题开始有了讨论的空间。 “现代历史正变得越来越像一门学科。”
正是在这个契机上,马勇进入了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并深入参与了此后三十年近代史从政治到学术的转变。 这是时代的进步,也是思想的进步。 他主张:“必须把晚清史回归清朝,使清史成为一个完整的单位,使清史研究成为正典,就像研究唐史一样。”和明史,没有任何思想障碍。”
与同时代的许多著名学者不同,马勇的写作起步较晚。 对于20世纪80年代的“文化热”,他自称是旁观者和受益者,而不是参与者。 这与他所接受的教育密切相关。 在安徽大学、复旦大学读书时,他没有发表论文的愿望和能力。 朱惟正等资深学者也谆谆告诫,50岁之前不要写作,而要刻苦读书。
进入社科院后,院里的前辈们并不建议年轻人太早发表文章。 当时,近代史研究所的学术氛围浓厚,职称的评判并不需要以论文或书籍的多少来评判,而是以是否有真知灼见来评判,而这一切都是“凭本事”。老先生的感觉。”
自诩话痨的马勇坚持“只说不写”,刻苦学习了五年。 他补了近代史课,读了很多以前从未接触过的资料,包括一些港台书籍和旧报刊。 此时读书不是为了写作,而是为了理清问题。 算上在校的七年,他已经在替补席上呆了十二年了。 那是他一生中最专心学习的时期。 大量的阅读积累为后续的研究和写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学术三十年:寻找历史逻辑,努力理解文明史
马勇在《作为艺术的历史》一文中说,“如果一个历史学家不能持续地阅读和忍受孤独的沉思,那么无论他多么聪明,他也只能是一棵无根无源的树。” 止水的‘小聪明’。 历史研究需要建立在大量阅读和充分掌握资料的基础上。”
十几年不带功利的读书让他积累了知识。 最终,在近代史研究所前身张德新先生的提醒和调侃下,马勇打破了只讲不写的传统,于1991年开始了专业历史写作生涯。
短短几个月的时间,他集中精力撰写了《略析1911年后复辟帝制思想》、《评1911年后尊孔思想》、《黄老学与初汉社会》等。 《王朝》、《严复晚年思想演变的重评》、《文革后复辟思想的文化考察》、《李斯的思想品格与秦文化政策的得失》、《公孙弘》与儒学的复兴》、《清政府对戊戌变法的回顾与反思》、《民族主义与1898年的维新变法》等几篇文章,这些都是他研究多年、熟悉的课题。一口气写完,每篇文章约15000字,已发表在中国大陆、香港、台湾地区的学术期刊上。
20世纪90年代,政治保守主义一度成为学术界的主旋律。 受此影响,马勇潜心研究严复、梁漱溟等人提供的保守纲领及其在近代中国的实践。 后来,他在集体课题《中国近代通史》中承担了从甲午战争到新丑这段时间,这让他能够从政治史的角度重新思考当时中国人的追求和实践,以及如何看待中国近代史的发展。晚清帝国是由洋务运动演变而来,维新运动导致排外、新政,最后导致王朝灭亡。
接下来的二十年里,马勇的思考大致围绕着这些问题:晚清到民国演变的历史逻辑是什么? 各派政治力量、思想家、政客又有何打算? 到底是在什么时候实践和理想出了问题,导致一个古老的帝国不但没有通过改革获得重生,反而付出了王朝灭亡的代价? 他试图给出一个符合历史逻辑的答案。
他埋头于成堆的旧文件中沉思,深入历史细节寻找答案。 先后着有《中国近代文化问题》、《超越革命与改革》、《中华文明通论》、《近代中国研究》、《重新认识近代》等。 中国》、《新知背后:现代中国学者》、《晚清二十年》、《晚清四书》、《晚清笔记》等著作。 他在经济全球化、民族国家崛起和民主化出现的世界背景下审视中国的现代转型,并试图提供一套新的解释性话语。
同时,他还做了大量的个案研究,撰写了严复、章太炎、梁漱溟、蒋梦麟等人物的传记,并参与了许多人物的年谱和全集的编撰。 这些基本的编译任务费时费力,不计入计算中。 虽然已进入学术评价体系,但使学术界受益,也为后续研究者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马勇在今年出版的新书《近代中国的展开:以五四运动为基础》中,试图摆脱“小五四”和“大五四”的传统分析框架,将中国现代化转型中的五四运动。 放在明清的大背景下审视,从明清时期东西方不断的冲突与融合出发,开始探讨五四运动的政治文化必然性。 五四运动爆发的百年来,许多知识分子自觉地以“五四精神”为指导,自认为是“五四之子”。 然而,围绕五四运动的激进与保守、合法与非法问题,一直存在着争论。 不断地。 作为一位时刻关注现实的历史学者,马勇将五四问题与中国的现代化转型并列起来。 同时,他摒弃了以往一些学者以政治立场为先的做法,将五四运动置于更长的历史时期和全球语境中。 在文化化浪潮中进行考察,分析清末民初新教育、新文化、新政治、新伦理的诞生和发展过程。
在马勇看来,“只要人类继续存在,历史就会不断对过去的历史提出新的诠释,新的艺术类型就会不断被创造出来。 历史是一门常新的艺术和人文学科。 文化和知识永远不会固定在任何一种模式中。”
中国人历来十分重视历史。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历史就是中国人民的信仰。 孟子说:“孔子着《春秋》,而逆臣奸臣却畏惧。” 在马勇看来,从孔子到司马迁、司马光,乃至许多近代历史学家,都有着“情不自禁”的现实关切。 它试图以历史为工具,积极干预生活,为社会发展提供镜子和警示。
尽管有人说,“人们从历史中学到的唯一教训就是他们从来没有从历史中吸取教训”。 不过,马勇还是比较乐观的。 他认为,从长远来看,人类还是会从历史中吸取教训,从而走向文明。 发展和进步。 而他试图开辟中华文明史的尝试,也是基于这种美好向往的个人努力。
[问答]
新京报:一路走来,你坚持了什么?
马勇:一路走来,我主要坚持的是学会放弃、愿意放弃。 生命是短暂的,你一生中无法做很多事情。 坚持和放弃看似矛盾,但其实是一回事。 我很佩服那些将工业或行政与知识结合起来的朋友,但以我自己的评估,我可能会花一生的时间来阅读中国历史。
【旅客感言】
李莉(《东方史评论》执行主编,着有《求变者:回望与重访》、《转向公众》等):
马勇老师是我的“老朋友”。 在我们十多年的交往中,我们在公私事务上经常沟通与合作。 虽然他是历史专业的,但他并不是一个纯粹的“学院派”学者。 从小经历生活的艰辛,见证大时代的苦难,丰富了他的见识,也让他的性情变得十分平和。 马老师为人处事很少走极端,不为名利所累。 事实上,他并不需要靠写作或出版来谋生。 我想这种气质和心态无疑已经渗透到了他的治学之中。 无论是在学习上还是在生活中,他都养成了罕见的宽容和理性的风范。
20世纪50年代出生的学者普遍具有较强的家国意识,其学术研究具有清晰的社会问题意识。 马勇也是如此,他是少数能研究各种历史的人之一。 所谓“开拓”,首先是在时间上,从古代史到近代史,他都下了很大的功夫,著述颇丰; 其次,就研究领域而言,从“宗教”思想史到“务实”政治史、社会史,从儒家思想的古今演变到1898年维新运动、中日甲午战争等具体事件的研究1888-88年的战争和五四运动,都有独特的见解。 此外,他还能将宏大的历史叙事与具体历史人物的命运融为一体。 他可能是同时代写文字专着最多的学者之一。 其笔下人物有董仲舒、蒋梦麟、章太炎、梁漱溟、严复等古今人物。 。 同时,他还参与了一些人物年表或选集的编撰。 这些基础资料的整理无疑将使整个历史共同体受益。
特别36-特别37版/新京报记者 徐雪琴 撰稿
本页摄影/新京报记者 徐雪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