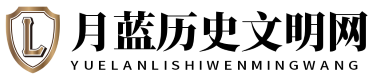黄进兴重识穿梭异文化空间的人物以梁启超王国维傅斯年为例

新史学的倡导者虽然抛弃了传统史学,但为什么他们仍然推崇传统的史学考证技术呢? 这种情结不仅见于赋,也见于梁启超、胡适。
兰克的史学在世纪之交面临着被欧洲或德国强敌包围的困境; 然而,一些历史精神,特别是对于来自其他文化的游客来说,仍然是新奇和令人欣慰的。
近年来,中国大陆在文史资料的整理和发展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使许多学术问题的认识更加深入和准确。 就我个人关注的史学而言,华东师范大学长期的历史工作积累是令人印象深刻的。 在台湾,由于先天素材的不完备,始终饱受“文学匮乏”的困扰。 举个例子:我亲自探索“清末民初道德意识的转变”,感受特别深刻; 主要在当地留存的现代教科书非常有限。 法医鉴定并不容易。 因此,我更加羡慕中国大陆近年来积累的文史研究工作。
然而,在这个来之不易的经验证据的基础上,如何进一步推进或扩展其研究成果,却是时常萦绕在我脑海中的考虑。 如果说“知己知彼”是全面把握历史问题的必由之路,那么除了广泛收集各种来源的中文资料外,“知己知彼”仍然是必要的,因此了解跨文化人物的文化状况在对方是不可或缺的。 首先必须提到的是,我的前任本杰明·施瓦茨教授(Benjamin I. Schwartz,1916-1999)多年前就出版了他的比较思想史经典著作:《寻找财富与权力:严复与西方》威力:严复与西,1964),充分论证了这一方法。 顺便说一下,石华慈教授的见解独到,因为他对中西思想史有深入的了解。 他特别提醒严复,他去英国深造时,并不是一张白纸,而是有先入为主的眼光,对西方经典做出了独特的解读和解读; 他将施的西方原文与严氏的中文译本进行比较后,梳理了严氏理解的差异和文化意蕴。 从先贤那里获得以前从未分享过的见解是令人耳目一新的。
另外,以我近年来探讨的三个案例:梁启超、王国维、傅斯年为例。 他们三人都有沉浸在不同文化中的经历,也恰好与兰克的历史有着不同程度的联系。 我想简单地阐述如下:
首先,以梁启超(1873-1929)为例。 梁氏学问通晓古今中外。 他多次在日本停留,后来又到欧洲和美国考察。 纵观梁启超一生的政治和思想,经历了很多变化,他毫不犹豫地说“即使是今天,也不会是昨天的我”。 这对史的历史发展的评价也不错。
本世纪初,扶桑人叶间直树利用天时地利,集合众人的智慧和努力,探寻梁氏思想形成的日本渊源。 成果是相当可观的,具有借鉴意义。 另外,上世纪末,我曾毫不犹豫地对梁氏史学进行过一番探索,下面简单叙述一下; 》(1922)名满天下。从所有事实来看,梁祝的影响显然是任何人都无法比拟的。就连视梁为学术对手的胡适(1891-1962)也称赞此书为“任公的著作”。最佳作品”,更不用说其他人了。那么梁先生独特的号召力和贡献是什么?
据梁启超早年多次旅日介绍,他深受当地文化和学术氛围的影响,思想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因此,了解当时的思想状况,有助于了解梁氏思想形成的背景。 如前所述,梁氏著作中所蕴含的历史原理,实际上是建立在西学历史知识的基础上的。 就我个人而言,我以日本汉学大师桑原幸三(1871-1931)对梁氏代表作《中国史学研究方法》的书评为分析起点,更能体现梁氏史学的意义。
总体而言,桑原高度肯定了该书的学术价值,并相信该书将为中国史学的创新发挥作用。 不过,熟悉日本史学界的人,都熟悉德国人恩斯特·伯恩海姆(1850-1942)的《历史导论》(1905年)、日本史学家恩斯特·伯恩海姆博士的《历史研究方法》(1903年出版)等书。坪井。 ,本书无需参考。 不过,他随后表示,梁启超书中引用的中国历史事例在其他书中是独一无二的,所以所有研究中国历史的学者都应该多加关注。 鉴于桑一直以来不太关注中国学者的研究方法,获得这一认可实属不易。 为了了解真相,必须驳斥桑原的评论。
日本比中国更早关注西方史学。 1887年,德国兰克(Leopold Ranke,1795-1886)学派弟子路德维希·里斯(Ludwig Riess,1861-1928)开始在东京帝大学教授日耳曼史学。 随后,日本留欧学生纷纷回国,以东京大学为基地,教授严谨的历史批判。 当时西方史学家以德国史学为范本,日本史学在西化过程中也不可避免地表现出同样的现象。 桑原提到的坪井博士就是上述的代表人物。 坪井的全名是坪井藏马三(1859-1936)。 他早年旅居欧洲,深受德国史学影响。 回到日本后,他在东京帝国大学任教多年,教授历史方法和政治外交史。 它是日本等级史学的旗手。
桑原提到的另一位学者布伦纳姆是德国史学方法的大师。 1889年,他出版了《历史学手册》(Lehrbuch der historischen Methode und Geschichtsphilosophie),被公认为兰克史学的结晶。 在西方史学发展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当时兰克史学的反对者卡尔·兰普雷希特(Karl Lamprecht,1856-1915)说:“史学发展的重要里程碑是伏尔泰、布伦纳姆和我自己”。 这是显而易见的。 】 桑原先生所说的《史学概论》,顾名思义,应该是他1905年出版的《历史概论》(Einleitung in die Geschichtswissenschaft)一书。 《岩波文库》的日文翻译。 桑原的评论意味着梁氏书中所推崇的历史原则并没有超出布伦纳姆的体系。
再次,致力于历史学多年的杜维云教授也指出,梁氏书中的历史观有很多值得借鉴的地方。 据该书作者介绍,朗格卢瓦(Charles V. Langlois,1863-1929)和塞尼博斯(Charles Seignobos,1854-1942)是法国日耳曼史学的重新弟子。 在法国史学界,《史学原理》与布伦纳姆的著作享有同等地位。 由于同源,它们可以被视为兰克史学在方法论上的最终表述。 因此,无论梁氏史学来自何方,都可能与当时的西方史学有着密切的联系。 继俊之后,吴国义先生进一步指出,梁启超最初的新史观颇受日本浮田一民(1859-1946)《史学通论》的启发。 据曾就读于耶鲁大学的浮田一民介绍,当时正值美国流行“科学史”的时期。 他与坪井九马三苏并称为世纪之交日本等级史学的两位倡导者。 总之,杜、吴的论点都是基于文本的整理和比较,与桑词中对方的实质性主张相互呼应、互补。
然而,仅靠西学的传播并不足以说明梁氏著作的成功。 否则,西学造诣尤深的何秉松、杨洪烈(1903-1977)的历史著作应该稍好一些。 事实上,他们在未来将会变得默默无闻。 此时,桑原智藏对梁氏国史造诣的钦佩,颇有几分教益。 梁先生的文史文化博大和谐,高人一等,能够融会贯通中外文化,毫无障碍。 这项移植工作看似平凡,实则难度极大。 后来的学者虽然在理论层面有所创新,但在理论的完善程度上还存在很大差距。 换言之,“中国史研究法”引起了广泛关注,并且长期不衰。 就是将西方史学与民族历史知识融会贯通的能力。 这一成就至今仍是罕见且无与伦比的。 为此,桑原对奎主未来发展的两段评价引人深思。
以王国维(1877-1927)为例。 王氏早年与西方哲学的斗争是后人津津乐道的壮举。 然而,三十年后,他毅然放弃了对西学的追求,转而专攻国学。 果然,他创造了伟大的事业,为后人所向往。 ,羡慕。 然而,他个人研究的转折和破裂却在不经意间留下了一个亟待解决的学术案例。 因此,如果没有康德哲学文本的直接证据,就无法把握王氏这一时期的思想和变化。 过去,治疗常常让人们有一种被困在幕后的感觉。 精神史学家常常避免阅读康德的著作。
确实,康德的哲学著作是出了名的难读、概念抽象、复杂。 不仅哲学家认为它们令人畏惧,更不用说以经验为导向的历史学家了。 但俗话说,进不了虎穴,就捉不到虎崽。 如果不能直接欣赏他的作品,就如同古人嘲讽的“告诉塔命运之轮”一样。
总之,王国维接触哲学纯属偶然。 他与康德哲学的四次斗争的故事早已为学界所熟知。 最终,他通过叔本华的解释,领会了它的要旨。 虽然王先生之前对康德的论文有一定的了解,但似乎很难掌握康德文本本身复杂的论证程序。 但总体而言,王对德国唯心主义的理解与当时日本学界的理解并不相符。 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学界接受德国哲学的时间早于中国,康德、叔本华的思想逐渐深入人心。 总之,康德的“批判哲学”走向了西方哲学的“哥白尼革命”; 它把原本被视为基本的、普遍的理论的形而上学转变为“认识论”的利器,并超越了传统形而上学本体论的形式。 王国维对此深有体会。 例如,他曾断言:“他(汗德)钦佩形而上学的不可能,并想用知识论改变形而上学”。 在重新阐释和评价中国传统哲学问题时,他也效法康德的“批判哲学”,运用“先验辩证法”的技巧,解决了中国传统哲学的命题。 他提炼出中国哲学中讨论最多的三个概念:“性”、“理”、“命”,以独特的方式加以阐述,写出了《性论》、《说》、《元命》三篇非凡的著作。
他所持的崇高观点源自康德的教义——不要混淆“形而上学”和“经验”讨论的不同范畴。 这是对他的特别表彰,以免后世学者对此进行“无用的讨论”。 这在当时确实是一个具有开创性的论点。 唯一值得一提的是,王国维在《签名三十》中毫不掩饰这一点。 他曾经读过《纯粹理性批判》中的《先验分析》,没能读完,就退学了。 但在近期的《论自然》等几部著作中,他可以自如地运用“先验辩证法”的推论来分析中国古典哲学命题。 他对康德哲学的理解能力显然是不同的。 【请注意,本文使用的康德英文译本并非王国维读到的英文译本。 “先验分析”(或译为“先验分析”)是《纯粹理性批判》的第一部分,“先验辩证法”(先验辩证法)是第二部分。 在逻辑理论中,首先要懂得“先天分析论”,才能领会“先天辩证法”的妙处。 但也有学者认为,“先天分析论”是书中最难理解的。 ]
另外,在《原命》一文中,王虽然假装解决康德的问题,但他能够与康德不同并提出异议,认为“责任”概念有其自身的价值,而不需要预设“意志自由”关于“为了翅膀”。王某的观点真假不重要,但这表明他逐渐有了信心并做出了选择,不再听从别人的说法。后来,王某一度认为自己无法理解的原因是康德则认为康的说法“站不住脚”,前后对比,王就像两个不同的人。
如果王先生确实跟随康德的研究思考中国文化相关问题,那么他这一时期出版的代表作恰恰揭示了他的阅读轨迹。 例如:《论自然》(1904)和《解释》(1904)对《纯粹理性批判》; 《原命》(1906)到《实践理性批判》; 最后是《判断力批判》中的一篇文章《古雅在美学中的地位》(1907)。 它们所涉及的问题都与“三个批判”一一对应。
这里,王国维的哲学需要稍微分析一下。 他坚持“纯粹哲学”,并将其他哲学视为混合体。 他曾批评一时成名的严复“崇拜英国功利主义和进化论哲学,兴趣不在纯哲学”。 因此,他算不上优雅。 王主张知识的最高满足必须通过哲学来追求。 他紧紧抓住叔本华的思想,说“人是形而上的动物,但却有形而上学的需要”,因此他把叔本华的形而上学视为“纯粹哲学”的典范。 他认为哲学是“无用的学问”,只能与美丽的艺术相比较,两者都是人类文化的最高结晶。 他还感叹,在中国,“没有纯粹的哲学,最完整的只有道德哲学和政治哲学”。 梁启超、严复因官职的缘故,一心追求世间的实用知识,而被他所鄙视。 他直言:“要发展学术,必须把学术当作目的,而不是手段。” 而中国人“为学术而读书”的,还不到千分之一。
一般认为,王国维于1911年再次东渡日本,经罗振玉劝说,改弦易辙,毅然放弃哲学,走上了研究国学的道路。 不过,我个人推测,在此之前,他可能还没有放弃追求西方哲学的想法; 不然的话,他也不会不厌其烦地奔波劳累,将那些与哲学有关的外国书籍带到日本,暂时存放在京都大学的图书馆里。 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也许是,王一旦长期游历,以他的聪明才智和求知热情,就会知道当时日本和西方哲学研究的水平远远超出了他的能力; 要想学有所成,人尽其才,“归国学”是正确的选择。
总之,王国维的哲学著作或许仅止于现阶段,有其时代意义,但真正的影响力和未来的学术发展是他接受西方史学、与国际汉学接轨的契机。 中间最重要的人物不是别人,正是他的师父藤田丰八和共同培养他的罗振宇。
王国维接受兰克史学,并受到藤田的影响。 藤田毕业于东京大学。 当时,正值兰克的关门弟子拉斯前往日本授课的时期。 藤田这一代的许多汉学家都受过他的教导,受到兰克史学的洗礼。 这也是日本近代史学转型的契机。 特别是当时日本“东方史”的研究倾向是向西方求助而不是向中国学习。 王第一次了解兰克的历史是因为藤田请他写序。
总之,兰克史学对日本或中国的“新史学”最重要的启示,无非就是强调“原始史料”和史料的“系统性”。 这一点在藤田或王国维的历史实践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 王曾称赞藤田对中国古代棉花工业的分析。 它的优点是很好地利用了很多我们这一代无法使用的材料,这对我们自己来说是一个遗憾。 需要注意的是,王国维的学术生涯是从研究西方哲学开始的,所以尽管他接触过兰克的历史,但其影响一时并不明显。 但一旦进入文史领域,他的影响立竿见影。 例如,在编写《宋元戏曲史》之前,他首先查阅了大量资料,编撰了《宋大曲考》、《游玉录》、《戏曲源流》和《录曲玉谈》( 1909)等,这或许可以视为兰克史学的典型做法。
王国维踏入国际汉学的另一位领军人物是罗振玉。 证据之一就是他年轻时并不喜欢《十三经注》。 他一经受新思潮的洗礼,便踏上了西学之旅,一去不复返。 此时,因罗石劝他“专攻国学”,他一改旧习,抛弃所学; 遵循罗老师小学训诂的要求,勤奋学习《十三经注》,为以后董力的国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基础。 这虽然让他了解并继承了清代的学术知识,但仍不足以充分了解他日后取得伟大成就的背景; 正如他的弟弟王国华(1886-1979)所说:“兄长的学术方法虽然与钱嘉、贾前辈有相似之处,但超出了钱嘉、贾前辈的范围。” 此外,王氏多年的挚友金良(1878-1962)更进一步说,他“尤善用科学新法,领悟董氏旧学,其术学之精深,令所有学者都叹为观止”。国内外都称他为“。”
另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是,罗氏和藤田无私地推荐王先生与日本和国际汉学界直接讨论和交流,让他接触到及时的学术话题并展示自己的才华。 总之,无论是在独到的见解上,还是在开拓新的领域上,未来王都一定能够以自己的方式脱颖而出,受到大家的期待。 最后,他引用了王氏的学术同伴鹿野直树的评论,总结了王氏一生的学术特点:
作为一个学者,王俊的伟大和优秀就在于他能做到中国老一辈大儒家能做到的一切。 ……但由于他学过西学,他的学术研究方法比中国历代伟大儒家的研究方法更加可靠。 也就是说,他对西方的科学研究方法了解得很透彻,并运用到国学的研究中。 这就是王俊作为一个学者的优秀之处。 (《王静安回忆》)
总之,卡诺所谓的“西方科学研究方法”无非是兰克的史学,被视为世纪之交“科学史”的标准。 作业就是说,王家受兰克史学的影响很大,虽然不在中间,但也相差不远了! 因此,西方哲学对王的影响是暂时的,而西方史学的影响则是永久的。
最后,以傅斯年(1896-1950)的史学为例。 他原本在英国留学,后转学到德国深造。 后者深入研究历史学和语言学,这是一个成熟的阶段。 傅斯年留下的《史法讲义》一书残缺不全,很难全面了解。 书中与兰克直接相关的内容很少。 因此,我们必须寻找其他方式来检验他与兰克史学的关系。 西方思想史上有一个例子,就是“维特根斯坦的维也纳”。 本书的两位作者用“间接证据”来梳理维特根斯坦哲学事业的基础。 由于维特根斯坦从事语言哲学的原因一直是西方现代哲学中的一个谜,史蒂芬·图尔敏和他的学生艾伦·贾尼克借用了卡尔·肖尔斯克的《世纪末的维也纳》(Fin-De-Siècle Vienna)研究《:政治与文化》以此为基础,凸显了维也纳当时所处的文化危机,从而证明了维希纳从事语言哲学的意义。这部作品个人印象深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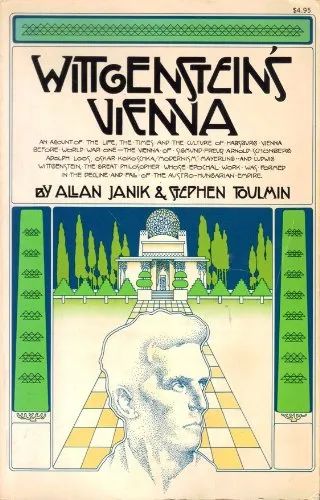
Jenic 和 Toulmin 维特根斯坦的维也纳 (1973)
总之,“周围证据”并不像“直接证据”那么简单,而是需要一点想象力。 其作用主要是间接“对比”而不是直接“证明”。 以傅斯年和兰克的关系来看,傅斯年所说的关于兰克的话确实是相当有限的。 但如果硬要以此来探究他与兰克的历史渊源,我们就难免会陷入禅宗所说的“死在字下”的执念。 因此,我们必须寻找另一个渠道来一睹真相。
傅斯年多次举起双臂,高喊“史学就是史学”、“史学就是史学”之类的话,意在炫耀自己的历史观。 然而,这些鲜明的口号日后却意外地成为了别人批评的对象,甚至被“历史学派”嗤之以鼻。
如果要纪念中国近代史的里程碑,有两篇大文章是不可忽视的:一是梁启超1902年发表的《新史学》;二是梁启超1902年发表的《新史学》; 另一部是傅斯年1928年出版的《历史语言研究》。第一部分是气氛发展的开始,第二部分是组织的宣言;两者有一个共同点。对以后中国史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此前,笔者对梁氏的“新史学”略作研究,在此不再赘述。 《语言学》无疑是傅先生一生治学的纲领,也是傅先生史学最完整的表述。而学界最流行的口号就是:“历史不过是史料之学”,及其优缺点然而,要理解这一论点,首先要把握傅先生对历史的定位和他所赋予历史的任务,然后转向他所引入的“史料”这一新概念。
综上所述,世纪之交的欧洲或德国,兰克(1795-1886)的史学面临着强敌四面围攻的困境; 但仍然新颖可喜,被傅吸收或继承了。
读者只要稍微对比一下兰克的论点,傅氏史学的来源就会豁然开朗。 兰克的《拉丁和日耳曼民族史》(1494-1514)一直被公认为现代西方史学的里程碑,其序言尤其为学术界所熟知。 兰克说:
历史曾经被赋予评判过去、指导现在、造福未来的职责。 本书并不希望有这样的需求,它只是对确实发生过的事实的陈述。
兰克诉诸历史只是为了“陈述真正发生过的事实”(wie es eigentlich gewesen)。 乍一看,他的语气似乎极其谦虚,但实际上并非如此。 这句话是近代历史的精神标志。 它象征着历史独立的宣言。 从此,历史不再是神学、哲学的奴隶,也不再是文学、艺术的附庸。
“历史事实不言而喻”,是傅斯年反对“疏浚”的论据。 傅坚信:
历史的对象是史料,而不是文字、伦理学、神学、社会学。 历史的工作是整理历史材料,而不是构建艺术,促进交流,或者支持或推翻这个运动或那个学说。 (《历史方法导论》)
如果我们仔细观察这些学科的底层秩序,就不难发现,傅氏思想所反映的其实是西方史学演变的一个缩影。 他避免提及传统旧派压制史学的“儒家经典”。 相反,他强调了西方文化的独特产物:“神学”和“社会学”,这确实是有趣的线索。 这些学科都在史学领域留下了压倒性的记录,所以傅老师重申史料是历史学的主体。 只要把史料整理出来,真相就会水落石出。
兰克一生走遍了欧洲各地,孜孜不倦地寻找和梳理原始档案。 他所撰写的历史著作无非是他自己治史哲学的最佳实践。 他的学风正如一位下世纪中国追随者傅斯年这样勉励自己:
我们不是学者,我们只是用手脚在寻找东西! (《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宗旨》)
傅先生急于寻找的“东西”是“新材料”,而直接的史料是重中之重。 与传统文士静坐书房不同,傅为中国历史学家塑造的充满活力的新形象无非是传入西方的兰克。 【虽然我推测傅斯年塑造的新历史学家形象源于兰克的学术特征,但这句话似乎是英国历史学家乔治·麦考利·特里维廉(1876-1962)传下来的。 崔威廉于1903年出版了《重新发现克里奥》(注:克里奥是历史女神),旨在反驳另一位历史学家JB伯里(JB Bury,1861-1927)的科学史学。 1913年崔氏修改并在《克利奥:女神》中重新出版。 文章将竞争对手的思想流派描述为“收集‘事实’——你必须下到地狱,上到天堂才能得到它们。” 傅斯年笔下的史家具有动态的求索理念,这与传统学者局限于读经、读史不同。 ]
兰克一生走遍欧洲,孜孜不倦地寻找和梳理原始档案。 他所创作的历史著作无非是他自己的历史哲学的最佳实践。
说实话,重视史料,特别是原始资料,并不是从傅斯年开始的。 此前,梁启超、胡适曾受西学影响,已屡次阐述; This argument was radicalized and went on to argue the “priority of historical materials”, achieving his view that “historical materials are historiography”. Therefore, in terms of academic theory, Fu Sinian simply summed it up: “History is the study of historical materials.” Because he believed:
Anyone who can study the material directly will make progress. Any indirect study of systems studied or created by predecessors, without extensive and detailed reference to the facts contained, will lead to regression. (同上)
Based on this, Fu also distinguished the difference between “scientific research” and the past “research of academic scholars”, and then founded China’s first professional historical research institution: “Institute of Historical Language”. It is no wonder that among Western historians, Fu especially admired the historical achievements of Lan Ke (Run Ke) and Theodor Mommsen (Theodor Mommsen, 1817-1903); as for Chinese historiography, he valued the historical methods of Sima Guang and Qian Daxin. In terms of the application of historical materials, he certainly depreciated Ouyang Xiu’s “History of the Five Dynasties”, but on the other hand highly praised Ouyang’s “Jigulu” as “the real skill of modern historiography to study direct materials”. The reason is that it caters to the level of historical material research required by Western historiography.
The above just solved a mystery of modern Chinese historiography: why did the advocates of the new historiography abandon the traditional historiography, so why did they appreciate the traditional historical research? This complex is not only found in Fu, but also in Liang Qichao and Hu Shi. For example, although they despised the historical views contained in “Zi Zhi Tong Jian”, they praised Sima Guang’s historical research alone, which represented the acme of historical research work-the textual research of the Qing Dynasty was even more highly praised. The only difference is that research work has been impacted by Western historiography and must be refocused: traditional classics are no longer the authority of the final appeal,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istorical materials and facts constitutes the focus of new historiography. This is what Fu Sinian insisted, “If you hold the concept of ‘extremely rich in records and reliable in literature and art’, you can at most be a Cui Shu, and you will definitely not be a modern historian” (“Lecture Notes on the History of Ancient Chinese Literature” ) correct answer.
In a nutshell, Liang Qichao, Wang Guowei, and Fu Sinian all had rich experience traveling through different cultures. Therefore, in addition to reading their Chinese works in detail, they must go deep into the places and know the different cultures they have experienced in order to fully grasp the other cultures. The original form of thought. It is indispensable to understand “the other side” again, but it is still necessary to read the author’s original Chinese works carefully, because foreign cultures are vast and boundless, and visitors are always limited by preconceived concerns, so they can only “” There are three thousand weak water, but only one scoop is taken.” Therefore, the Chinese writings preserved by visitors are indispensable clues.
This article was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Wenhui Scholar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