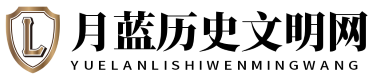历史的真实性与历史学家的历史责任
人们总是选择性地记住复杂的历史事件。 我们看到的历史是“为现实重构”的历史,也是历史不完整的一面。 简而言之,历史大体上是可靠的。 然而,个别事件已被不同程度地改写和重塑。 有的还离事实不远,有的却已经面目全非。 如何更好地保存历史事实,为现实提供有用的借鉴,即“求真”与“应用”,是贯穿中国古代史学的两个重要问题,也是中国古代史学家努力完成的两大任务。 。
历史的真实性——从“泰伯逃吴”的传说开始
有时我们不得不承认,真正的过去已经永远消失了,而我们记住的过去是为现实而重建的过去。
台湾学者王明科在《中国的边缘——历史记忆与民族认同》一书中,重新定义了人们经常使用但难以准确描述的“民族”一词。 他认为,种族是一群人的主观身份范畴,而不是特定语言、文化和身体特征的组合。 正如家庭重新排列家庭照片、重建家谱以维持特定的记忆一样,一个民族也需要不断调整其集体记忆以适应现实的变化。

《史记》记载的“叔逃吴”事件就是集体记忆调整良好的一个例子。
泰伯吴及其弟仲雍都是周太王的儿子,王季礼的兄弟。 季礼贤,与圣子常,太王欲立季礼、常,于是太白、仲雍到荆蛮,纹身剪发以示无用,以避季礼贤。 姬立国若立,则为姬王,昌为文王。 太伯之父景满,自号吴。 景满益之,遂归于钱于氏,立为太伯吴。
“泰伯逃吴”事件与许多非华裔少数民族追寻的祖先事迹一样。 比如所谓的“楚国祖先出自颛顼高阳”、“秦始祖,颛顼帝后裔,女修”,真实性颇令人怀疑,很难想象这些中国人眼中的“夷人”,与中国人有着共同的祖先,他们的家谱构建得如此完整、细致。

对于当时的中国国家和吴国来说,深入调查“太伯弹吴”的真实性既没有必要,也没有意义。 无论事件的真实性如何,“太伯逃吴”的传说显然拉近了中国与吴国、吴国与华夏之间的距离。 在此背景下,泰博成为了两方之间的巧妙纽带。 泰伯事迹的真正含义是中国国家和吴国共同承认并允许代代相传的,是民族身份的双向象征:被吴人借用,以强调他们是中国人,并表达了对中国国家的尊重。 这种接近和展现善意也是中国政府用来证明这个土著家庭是中国的臣民之一而不是“野蛮人”的重要方式。
因此,在这种利益平衡机制的影响下,吴人的真正祖先可能被泰伯吴所取代。 这段记忆在代际传承中被延续、巩固、美化,最终诞生了“泰伯奔吴”的美丽传说。 这个传说的构建,对于吴国、对于中国、对于当时的人民、对于他们的子孙后代,都具有积极的意义。 历史记载中充斥着这种虚构的民族迁徙作为历史记忆。 但在这个为了更大利益而人为选择和改写民族记忆的过程中,历史真实性显然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了牺牲品。

吴人追溯泰伯为祖先,是为了获取实际利益。 这个案例并不是一个孤立的案例,而是许多民族所采纳的生存智慧。 改变记忆的事件不仅存在于种族群体中,而且更常见于较小的个体——家庭,并且发生在每个人身上。
对于复杂的历史事件,人们总是有选择地记住——有些事件被不断强化、固定、代代相传,而有些事件则被刻意遗忘。 我们看到的历史是经过前人多次加工的历史。 这是一部“为现实而重构”的历史,也是一个不完整的历史侧面。
幸运的是,我们仍然可以利用这些不准确的历史事实来试图还原一个普遍可信的历史情况,防止我们对历史事实的整体把握歪曲真相。
《史记》记载孔子“作《春秋》,笔是笔,伐是伐,子夏弟子不能称道”。 “比”是在《春秋》原记载中加上的,“切”是相反的。 原《春秋》记载有删节。 孔子在历史叙述中并不直接讨论,而是通过修辞手法的选择、详细的描述、材料的选择来隐藏赞扬和批评。 后人称之为“春秋书写法”。 这种书写方式在中国历史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影响很大。
无论《春秋》是否出自孔子之手,其高超的选材和叙事技巧足以证明,早在先秦时代,古人就已经能够熟练地选择、加工和创造历史事件。 。

每个人的每一次历史叙述,都无意识地改写和加工了历史事实,并有意无意地融入了自己的道德评价和思想倾向。 历史长河中的历史叙述者就像装配线上的加工者,历史事实就像装配线上的原始零件。 每一次加工,它们都会改变原来的面貌。 最终它们会由粗糙变成光滑,其使用价值也会随之改变。 虽是上升了,但终究不是之前的那张脸了。
历史事件的真实性随着时间的流淌而被打磨、消磨,这是一个不可避免的、不可逆转的历史过程。 即使历史叙述者和历史记录者想要不犯任何错误地记录历史现实,也是不可能的。 更何况,这并不是他们很多人的初衷。 那么,历史事实的转变就不可避免了。
一般来说,历史事实是有选择地、有框架地保存下来的。 即使跨越几千年,我们仍然可以依靠这些主线,努力还原当时社会的整体面貌,并取得良好的效果。 但就具体而言,每个历史事件的真实性却参差不齐。 虽然很多事件仍然保持着良好的真实性,但也有很多事件被不同程度地改写和重塑。 是的,有的东西是从无到有创造出来的。
这种无处不在的改写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几代人对某些历史现象的印象,多次微小的修改甚至可以导致某些重大事件的“重塑”。
总之,一般来说,历史总体上是可靠的,其真实性必须予以积极评价。 然而,个别事件已被不同程度地改写和重塑。 有些与事实还相差不远,有些则已经面目全非。

二、“求真”与“应用”——历史学家的历史责任
虽然历史事实的消失是一个自然且不可逆转的过程,但人类的努力无疑是能够缓解这一过程的有效措施。 对于古往今来有抱负的历史学家来说,如何更好地保存史实是必须面对的问题,必须努力给出好的答案。 这也是贯穿中国古代史学的一个重要问题,那就是“求真”。
在《论语》中,孔子明确表达了他追求史实的严谨态度。 如果没有足够的材料来进行有效的描述,那么就没有必要记住它。 “我能描述夏朝的礼节,但不能征服他们。我能描述殷朝的礼节,但不能征服宋朝的礼节。没有足够的文献,所以我可以征服他们。”
《左传》中,还有极力保存历史真实、不畏强权的“上古良史”董虎。 可见,中国史学“求真”的传统源远流长,为历代史家所继承和践行。
马迁的太史氏“求真”之意在《史记》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这不仅体现在其理论阐述中,而且广泛存在于他的历史写作实践中。 就其理论层面而言,司马迁在《史记》的《报任安书》中谈到了他写书的目的,就是“研究天人关系,了解古今之变”。现代,并形成一个家庭的故事。”
司马迁想要探索自然现象与人类社会的相互作用,了解从古至今的历史发展和演变,形成自己的一套独立的理论,探究历代王朝兴衰的原因。 要实现这一进步目标,识别和选择历史事件、力图还原一幅离原貌不远的历史图景的基础工作就显得尤为重要。

在实践层面上,不难发现司马迁追求史实的努力。 在长安读书十年,二十岁时游历各地。 他走遍世界各地寻找名人的遗物,历时十几年。
系统的知识学习和长期的访问,极大地拓展了司马迁的历史知识,为他后来撰写《史记》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在《史记》的写作中,司马迁把史实放在了很高的位置,体现了严谨的记录精神。
司马迁敢于面对现实,甚至可以打破常规去追求真理。 在写刘邦时,他并没有仅仅因为他是汉朝的开国皇帝而刻意歌颂他。 在他的笔下,青年时期的刘邦是一个“仁爱之人,好施,用心宽厚,但“不参与家庭生产劳动”的泗水“好酒好色”形象。亭长,豪爽、大方、圆滑,又有些慵懒。
在写项羽时,他并没有因为他最后的失败而低估他,而是从多个角度来描写他,构建了一个复杂的“西楚霸王”形象——勇猛无愧于天下男人,天生的战略家。 在推翻秦朝方面立下了赫赫战功,但他勇猛优柔寡断,错过了很多机会,从而导致叛乱、分裂,最后自杀于乌江。 同时,司马迁的叙述对象也十分多样,从经济历法到天文地理,从王公将领到百姓,从首都长安到周边国家。 《史记》可以说是一部“世界史”,或者说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作品。
通过这样多方面、多角度的描述,《史记》中的历史人物显得更加立体、真实,史实的还原程度更高,叙述也更加可信。

但对于司马迁以及中国古代许多杰出的历史学家来说,他们写历史的目的不仅仅是力求保存历史真实,而是着眼于“施于世”,用写历史来表达个人思想,提供各种现实参考。 深入思考,这也可以概括为他们写作的“意识”。 梁启超在谈及写《史记》的目的时曾说过,“过去史家写历史,往往带着超历史的目的,‘以历史事件为手段’,以展示自己的各种理想。”现代则不然。就像历史学家一样,他们为了创造历史而书写历史。” 我们可以将这种思想倾向概括为“求实”。
张学诚在《文史通义》《述教下》一文中谈到了历史书写的两种形式:注解和叙述。 “夫之智者,藏其往事,神者,知其来者。记往事者,不忘其事,写欲来者之兴也。故记往事,如智,写事”。知者,以效神也;隐古欲其周全,故其身一定,而其德方;知其来而欲决,则取之,故规则。不刚,而德圆”。
笔记的主要功能是保存历史,主要体现“求真”。 书写具有以史为鉴、启迪后人的功能,主要体现在“应用”。 在张学诚的写作中,《史记》与《汉书》有很大的区别。 俗话说:“微妙地说,左氏移书近,班氏移书远;钱氏文体圆用神,承于《尚书》;钱氏文风圆而用神,承于《尚书》;钱氏文风圆而用神,承《尚书》”。半石之风方正睿智,亦有官礼之意。” 《史记》文风圆神,其书写特点超过其笔记特点。 ,其“实用”性质就更加凸显。

司马迁以孔子编撰的《春秋》为典范。 ” 闻董胜曰:“周道衰,孔子为鲁匪,诸侯害其子,官雍智被杀。孔子自知其言无用,其道不实。两百四十二年来,他以为自己是天下第一,贬帝,退诸侯,讨好大夫,以成就王事。 子曰:‘欲录空言,不如见行中之深明之事。’”孔子《春秋》的主要目的也不仅是为了保存这段历史,也是为了记录这段历史。在这个天下衰落、大臣们经常弑君子弑父的乱世里写《春秋》。
其主要目的是用事件来表达道理,希望能够复兴世界秩序,起到告诫当代、警示后代的作用。 在这一宗旨的指导下,《春秋》的“用”性自然就凸显出来,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比“求真”更重要。 这一特点为司马迁所认识和继承,在《史记》中也有明确的体现。 太史公曰:“先祖云:‘孔子自周公死后五百岁就有了。从孔子死后到今天五百岁,谁能领导明朝,《正一传》,继春秋之后,这诗书礼乐之际?‘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这个意思!你怎么敢屈服? 这是真的。
“追求真理”和“推动实际应用”可以说是古代史学家的两大兴趣。 两者并不是分开的,而是有其内在的联系。 求真是基础,求真是为了实用。 求真也是根本。 要想以史为鉴、造福当今世界,首先必须在很大程度上保证历史事实的真实、准确。 如何妥善处理两者关系,是中国历史上长期存在的难题。 这也是衡量一本历史书优秀与否的重要标准。 在这个问题上,无数历史学家都做出了自己的“答卷”。 就司马迁个人而言,他的《答卷》无疑是一部不可多得的继往开来的佳作,可以成为后世学者的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