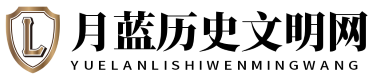新视角 马敏关于构建中国近代史学术话语体系的几点思考运用近代近代等概念
2022年第4期☆
* 本文为《中国近现代史‘三大体系’构建笔谈》系列文章第一篇。
中国近代史作为一门独立学科,自20世纪30年代建立以来,已有90多年的历史。 经过几代历史学家的建设,中国近现代史的学科体系已经日趋成熟,不同于1840年以前的古代史和1949年以后的当代史。但不可否认的是,由于这门学科诞生于20世纪“传播”时期, “西学东渐”的理论范式、问题意识、研究方法乃至话语体系都深受西方历史的影响。 因此,本土化转型尚未完全实现。
一些西方学者也对长期以来中国近现代史研究模式的“西方”特征进行了反思。 典型的例子是美国历史学家考恩的名著《发现中国历史——中国中心论在美国的兴起》。 他认为,20世纪70年代之前,西方对中国近现代史的研究基本上以“西方中心”理论为主导,可概括为“影响—反应模型”、“传统现代模型”和“帝国主义模型”三种模型。为此,他提出应建立基于“中国中心观”的研究模式,即从“中国内部”而不是从“西方”研究中国历史。译者林同其该书认为,“中国中心论对美国中国历史研究起到了真正的解放作用,其批判锋芒相当锋利。”然而,一些中国学者对柯文的新思维提出了质疑: 《发现中国历史》一书出版后,引起了国内读者对“中国中心论”的误解和追捧。 如果冷静地想一想,用西方概念和知识体系描述的‘中国’真的是‘以中国为中心’的中国吗?”
正是基于对上述问题的认识,以期从根源上建立近代中国本土化的“知识体系”。 近20年来,中国历史学家在词汇史、概念史、观念史、知识转化史等领域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学术研究。 讨论并取得了有目共睹的学术成果。 例如冯天宇、沉国伟等对来自日本的现代汉字术语和词汇进行了文化探索研究; 方为贵、李宏图、孙江、黄兴涛等的观念史研究; 金观涛、刘庆峰的概念史关键词梳理研究桑冰、张青、杨念群等的现代知识转型研究。这些研究通过对近代中国众多名词、术语、概念、思想、知识门类的系统梳理和文化探索,深入到思维方式的变化其背后的价值观念,揭示了与之相关的历史变迁,极大地丰富了人们对中国近代史的认识。
当前面临的问题是,如何在前人概念史研究的基础上,利用概念史“知识考古”中获得的大量材料和成果,自觉构建具有本土特色的中国近现代史学术话语体系。 大致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以中国为基础,对近代史上的术语和概念进行分类,明确其内在属性; 其次,以历史发展的总趋势为指引,确定哪些词语、概念和思想对推动历史实践和历史变迁起着更为关键的作用; 第三,它在“话语”分析的基础上整合了许多概念和概念,形成了既具有包容性又具有明确方向性和内在逻辑联系的话语体系。 。 这样做的前提是,需要为相关概念和思想的“历史化”、“社会化”、“系统化”提供更加宏观的理论思维框架,建立概念整合的相关标准和原则,并找到相应的整合方法。 。 研究人员已经对上述方面进行了讨论,但似乎还有进一步发展的空间。 我个人认为,就中国近代史学术话语体系的构建而言,沿着本土化、中国化的方向,大量的具体词语、观念、概念可以整合讨论为以下几对:更多核心概念框架(当然不限于这几对核心概念)。
一
时间维度中的“摩登时代”与“摩登时代”
据学者考证,“近代”、“近代”是中国古代就已经存在的概念,用来指代更近代的朝代或时代。 清末民初,随着西方史学传入中国,特别是在日本的影响下,“近代”、“近代”等古典概念获得了新的历史意义。现代意义上的分期。 “近代”通常指宋元明清以来(或仅指明清)的中国历史,而“近代”则多指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的中国历史。也有两者混合的情况。 作者倾向于明清近代论,但无意卷入“近代”与“近代”含义之争。 相反,他更关注与两者密切相关的“现代化”和“现代化”思潮如何影响和指导中国近代。 话语体系的形成。
众所周知,中国的“现代化”通常是指鸦片战争后中国在西方影响下发生的一系列经济、政治、社会和意识形态的变革。 这是一种“天崩地裂”般的时代剧变,或者说是“千年未有之变”。 然而,人们往往忽略了,在这场“变革”发生之前的两三百年(大约从明朝末年开始),中国传统农业社会已经酝酿着重大的社会变革:工商业空前繁荣。 、商业化、城市化、平民化、世俗化的经济社会趋势,以及实践学习和“新以人为本”思想所体现的启蒙思潮的兴起。 这一系列风起云涌的社会变革堪称“现代化”潮流——中国正在以自己的方式走出中世纪,步入现代。 如果说中国的“现代化”过程更多地反映了西方入侵造成的社会“突变”,那么“现代化”则更多地反映了源于中国社会内部的“渐进性变化”,一种传统的“自我改变”。中国近代史的发展应该是现代突变和现代渐变双重因素的结果。 越接近近代早期,内部渐进变化的影响和引导越明显。
因此,追寻中国近代史、构建近代史话语体系,必须仔细重构鸦片战争后的“现代化”与明清以来的“现代化”的内在关系。 我们必须重视“现代变革”的巨大作用,但也不能忽视“现代变革”在较长时期内的持续影响。 换句话说,西方的影响并不是导致中国近代变革的唯一因素。 许多从西方或日本引进的词语和概念如果脱离了明清以来“现代化”渐进过程的指导,我们就很难理解它们的起源和真正内涵。 。 例如“经济”、“工业”、“实学”、“实践”、“商业”、“商业”、“商人”、“财富”、“权利”、“金融”、“财富”、“资本” ”、“民主”、“民生”、“自治”、“权利”、“格致”、“科学”、“物质”、“博物”、“制造”等概念的内涵和外延都深受明清时期的实践思想。 它们是近代士大夫事业的延伸和拓展。 清末民初的知识分子在选择和创造这些词语和概念时,并不是任意的,而是受制于其固有的儒家价值观。 它们的渊源可以追溯到明末清初顾炎武、黄宗羲等人的启蒙思想。
二
空间维度上的“世界”、“万国”和“世界”
“近代”、“近代”一旦与“化”联系起来,就摆脱了单纯“朝代”、“朝代”的时间限制,除了历史时间之外,还具有历史空间意义。 1901年,梁启超借鉴西方历史分期方法,将中国历史分为三大时期:“上古第一史,从黄帝到秦统一,是中国的中国”; “中古第二史,自秦统一至清乾隆末,是亚洲的中国”; “第三个近代史,从乾隆末年到今天,是世界的中国。” 这一理论最重要的意义在于,它打破了传统的朝代更替史观,从中国与世界关系的角度重新定义了中国历史。
考虑到梁启超当时所说的“近代”实际上就是“近代”,他所指出的时间与空间相结合意义上的历史“中国”的区分,揭示了中西文化中“天下”概念的区别。古代中国和现代中国。 不同之处。 在中国古代(包括近代),大多数人的头脑中只有“天下”的概念,而没有“世界”的概念。 在浩瀚的宇宙中,中国不仅是地球的中心,更是“世界”的共同拥有者。 中国不仅通过“华夷之辨”、“改夏为夷”建立了中国与周边少数民族的关系,而且还通过“朝贡贸易”制度与亚洲周边国家建立了关系。 即使在明代中期至乾隆年间的“近代”时期,虽然也有少数西方人(如葡萄牙人)东渡,但总体而言,中国人的“世界”视野仍然局限于“中国”。 ” 本身以及亚洲周边国家中,只有在鸦片战争之后,中国才被迫被纳入到一个更大的世界秩序之中,并开始从“世界”转变为“万国”乃至“世界”,成为世界的中心。 “世界的中国”。
正如不少评论家所指出的,晚清从“世界”观到“万国”观的转变,首先体现在世界空间意识的变化上。 通过传教士传入的西学和林则徐、魏源、徐继社等人的地理书籍,人们逐渐有了“地”的概念,认识到中国不是地球的中心,而只是地球的一个中心。无数国家中的一个国家。 世界是地球合一的世界。” 其次,“国际秩序”概念逐渐取代“华夷秩序”概念。 中国正是在出使、经商、留学、参加世博会(当时称为“国家游戏”)的过程中,逐渐认识了由主权国家组成的现代“国际秩序”。如中国与外国的关系(外交关系)。 基本规则。 中国既是国际社会的一员,又是“殖民帝国”丛林体系中的弱势一方。 自诩为“中国中心”的过时“世界”观是弄巧成拙的。 20世纪初,更具多元性、竞争性和演进性意义的“世界”概念进一步取代“万民”概念,成为近代中国更为规范和流行的国际视野,中国历史进一步融入进入“世界”历史。
从概念史意义上看,从“天下”到“万国”、“世界”的演变,启发我们使用许多与国际谈判相关的词语和概念,如“蛮事”、“蛮情”、“太西”等。 》、《西方》与《东方》《地球》、《万国》、《外交关系》、《外国人》、《西方事务》、《中国与外交》、《中国与西方》、《谈判》、 “游戏”、“竞技”、“商战”、“公法”、“行会”等等,只能包含从古代、近代到现代。 只有在历史转型过程中,才能准确界定其实际内涵,观察其演变的规律和趋势。 中国进入“近代”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大量涉外新词汇、新概念的爆发。 从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初,短短几十年,对外关系概念的语义从讽刺的“野蛮人”到令人羡慕的“外国”,再到平等的“西方”和“西方”。西方的“外”,相关的词汇和话语组合也大量出现,其内部演变的原因颇为有趣。
三
社会维度中的“国家”与“社会”
从社会学意义上来说,广义的“社会”概念是指人类社会组织的总称,包括国家以及不同于国家、家庭的其他社会组织; 狭义的“社会”是指不同于国家的团体和组织。 由协会组成的社会组织。 除了上述两种含义外,现代西方社会概念还包括政治层面上连接国家和公民社会的“公共领域”和“公民社会”。
与西方不同,在中国传统社会,“天下,万物皆王土;陆地之滨,无非王臣”。 秦朝统一天下以来,君主政体至高无上。 公民社会的空间受到严重挤压,基本不存在西方意义上的“公共领域”。 一般来说,“国家强于社会”,而“社会”则被抽象、空心化,暂时“缺席”。 明清“近代化”进程中,随着公民阶层的崛起,国家财政状况的恶化,以及以黄氏为代表的“新民本思想”对专制皇权的批判宗羲、顾炎武、唐震等人,国家对社会对民众的控制放松,以君子为中心的公民社会逐渐形成。 近代以来,特别是甲午战争后,受西方自治思想的影响,各种民间组织得到了空前的发展,与之相关的“公共领域”也开始走向成熟。
中国现代政治话语体系的形成,正是在上述从“近代”向“近代”转型的背景下,围绕国家、社会及其互动关系的主轴线形成的。 关键词如“政治”、“政府”、“改革”、“改革”、“新政”、“宪政”、“宪政”、“共和”、“革命”、“民主”、“公民权利”、“ “民族”等,总体反映了从传统封建“王朝”向现代“民族国家”的转变过程; “团体”、“会议”、“学会”、“协会”、“协会”、“集会”、“演讲”、“君子”、“君子”、“君子”、“会员”、“公益”、“ “正义”、“公共利益”、“自治”、“民主”、“民治”、“权利”、“秩序”等关键词,大致反映了中国公民社会从“君子公共空间”的转变。从19世纪到20世纪初,从“先生们和商人”到“先生们和商人”。 公共领域”,进而转变为“公民社会”的过程。 同时,也体现了近代伟大转型转折过程中国家与社会的相互渗透、互动与博弈:公民社会一度空前活跃,最终回归“国家强于国家”的传统。社会”。
在中国近现代史学术话语体系的构建中,除了寻找上述核心概念和话语框架的相应融合,探索生成和演变的规律外,还必须着力探索中国近现代史学术话语体系的其他基本特征。现代话语体系的形成过程,如中西二元结构。 演化过程的特征、阶段特征等。
对于近代中西话语体系的二元结构特征,罗志天曾借用王国维的话概括为“道出二”,或者说中国新旧之间的纠缠与竞争。和西方; 金观涛、刘庆峰称之为“中西二元意识形态”。 这些见解很有启发性。 中国近现代史话语体系的构建必须坚持中国的中心地位,以中国化、本土化为根本导向,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脱离西方,忽视西方思想和话语的巨大影响。 近代以来,西方势力的入侵和西学东传虽然具有侵略性和强制性,但与中国传统农业文明相比,当时的西学毕竟是现代工业文明的产物,体现了现代工业文明的发展方向。人类文明的发展。 因此,向西方学习,大规模引进西方术语、概念、思想和话语是长期以来的必然,也成为朝野双方的共识。 正如梁启超所说:“当今地球上只有两种文明:一种是西方文明,即欧美;另一种是东方文明,即中国。二十世纪是婚姻的时代”。两个文明的交融。” 然而,学习和借鉴西方,并不意味着全盘西化,因为首先,当西方冲击中国时,中国不仅有几千年不间断的文化传统,而且传统本身也在发生变化。 中国人终究还是中国人,中国社会还是中国社会; 其次,中国对西方接受什么、不接受什么以及选择的标准都受到现有文化观念和价值标准的制约。 因此,中国现代话语体系的形成既需要“向他国学习”,又需要“向他国学习”。 它以中国文化为基础,选择性地接受和消化西学及其表现形式。 结果只能是“新学”“非中非西,而是中西合一”。 中西融合、古今融通已成为构建中国现代学术话语体系的基本原则之一。
其次,不可忽视的是现代话语体系建构过程的阶段性特征。 金观涛、刘庆峰曾从观念史的角度将中国社会的现代转型分为三个阶段:儒家式公共空间形成之前的阶段(明末清初至1895年)、儒家式公共空间形成之前的阶段(明末清初至1895年)建立民族国家(1895-1915),研究西方失败后的社会重建阶段(1915至今)。 相应地,社会思潮的演变也分为近代、近代、当代三个时期。 虽然这种划分是否恰当仍有待商榷,但对于探讨如何结合中国现代社会转型构建相应的学术话语体系,颇具启发性。
总之,构建中国近代史学术话语体系,必须拓宽历史视野,突破110年(1840—1949)的界限,在更大的框架、更长的时期内观察和思考。 至少要向上延伸到明清时期,特别强调明清时期社会文化的内部变迁; 还必须向下延伸到1949年以后,因为从旧中国到新中国还有一个历史过渡时期。 。 为此,结合中国历史与世界历史的内在联系以及中国近代社会的转型,中国近代学术话语体系的构建过程大致可分为:(1)明、明以来的“近代”时期。清朝(16世纪),地方话语的自我改造占主导地位。 到 19 世纪中叶); (2)1895年至1919年学习西方思想和话语的高潮时期; (三)1919年至1949年以学习西方为基础的本土话语全面重构时期; (4)1949年至1950年新旧话语转换的过渡期。 同时,从话语叙事转型的角度来看,大致包括明清以来的“现代”话语叙事(以治世思想为代表)、1840年以来的“现代”话语叙事和“现代”话语叙事。 1919年以来的“现代”话语叙事。1949年以来的“当代”话语叙事。研究范式很多,比如比较常见的“革命史”范式、“现代化史”范式、“民族复兴史”范式、“社会主义史”范式等。 ”范式等,是贯穿其中的阶段性主流话语范式。 一切与现代中国相关的词语、观念、概念的整合,都可以在这个更大的话语体系的框架内进行思考和建构。
总之,就中国近代史学科建设而言,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三大体系”建设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 其中,学科体系建设是基础,学术体系建设是核心,话语体系建设是前提。 之所以认为话语体系的构建是前提,是因为学科体系的宏伟大厦和自成一体的学术体系必须建立在自洽的话语体系之上,必须通过相应的话语体系来表达和传播。话语系统。 。 正如恩格斯所说:“一门科学提出的每一个新见解都包含着这门科学术语的一场革命。” 术语革命是实现学术理论革命的前提,但术语革命本身不仅仅是新术语、新术语。 概念的发明和移植,更重要的是必须依靠相应的理论框架来构建由术语、概念和范畴组成的完整的学术话语体系。 正因为如此,话语体系建设不仅是当前“三大体系”建设中相对滞后的“短板”,而且也成为中国特色历史学科建设的突破口。风格,还有中国风。
* 为了阅读方便,省略了注释和参考文献。 引用请参阅原文。
关于作者
马敏

马敏现任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所长、学校学术委员会主任委员。 曾任华中师范大学副校长、校长、党委书记。 主要兼职社会工作者有国家教材委员会专家委员、国务院中国历史学科评议组召集人、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会首席专家等。建设工程教材编写组、中国炎黄文化研究会副会长、湖北省炎黄文化研究会会长等。曾任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耶鲁大学、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访问研究员、访问学者。英国牛津大学。
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近代社会经济史、中国近代博览会史、中国近代教会大学史、1911年辛亥革命史。出版和主编学术专着20余部,发表学术论文100余篇。在《中国社会科学》、《历史研究》、《近代史研究》等期刊上发表中英文论文。 学术成果多次获得国家级、省部级奖励。

编辑| 黄蓉
评论 | 魏文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