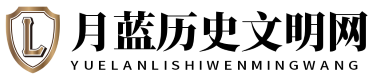138天的死亡漂泊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德国的潜艇战给友邦造成极大的损害,友邦船只“班洛蒙”号即是被德国潜艇击沉的。
那是1942年1 1月23日,“班洛蒙”号在距巴西海岸约莫1200公里的大西洋洋面上遭到潜水艇的袭击。两颗鱼雷钻进了它的身体。庞大的爆炸之后,“班洛蒙”号歪着身子,渐渐地沉入了海底。
“班洛蒙”号上有一个22岁的中国籍二等侍应生潘濂,他方才穿好衣服,船身便开始摇晃。一声爆炸震彻各层钢铁甲板,把他摔倒在地上。大股的水柱从破碎的舷窗射进来。当第二声爆炸响起时,潘濂才回过神来,明白“班洛蒙”号完了,它被鱼雷击中了。
潘濂抓起救生衣向甲板跑去,但救生艇已经开走了……
“班洛蒙”淹没了,其他的人除了死者都坐着救生艇逃跑了,在这片方才安静的水域上,只有潘濂,中国人潘濂,在水面上飘零。
幸运的是,潘濂发现了一只木筏。这是“班洛蒙”号上的木筏,由六个不透水的油桶构成,包在一个框子里,面积约7.5平方米。他奋力游近这个木筏,抓住它的救生索,然后从水里攀到两米半高的甲板上。木筏头尾有两个金属容器,盛了十加仑水。在一个大铁罐里面装着六个防水纸包的圆筒。这圆筒,就像过年时候放的火箭爆竹一样。这是信号弹。下面那层罐头和包裹里装着食物,有一公斤巧克力糖、五罐炼奶、一袋大麦糖和一瓶柠檬汁,另有干肉饼、牛肉干、面粉、糖浆、板油。潘濂尝了一点干肉饼,是咸的,味道良好。别的他还发现了一把长手电筒,灯泡发着光。潘濂以为自己有希望了。他把帆布拉出来,为自己搭建了一个蔽体。
恶浪淘天,大雨滂沱。
潘濂用筏上的短绳绑住了手腕,平躺在横档上,牢牢地靠着甲板。风波像野马一样激烈地撞击着木筏。短绳勒伤了潘濂的手腕,几块碎木片插进了潘濂的掌心,被海水一浸,疼得钻心。疼痛和严寒使得他满身颤动,肌肉抽搐,他却始终不敢活动。一旦被波浪冲进海里,那一切就都完了。
风波停止了,猛烈的阳光又来煎熬潘濂,把他的皮肤刺得像给蚂蚁咬了似的疼痛。他缩在闷热潮湿的帆布篷下,压碎了一块硬饼干,在碎块里加了点水,又加了点干肉饼作为调味。他没有一点胃口,但他知道自己必需吃东西。日出和日落时,他都逼迫自己费劲地咽下一点这种失去味道的食物。
就这样,一天过去了,两天过去了,三天过去了……第七天,潘濂发现海平线上现出了一个斑点。他的心脏都要停跳了,险些不敢呼吸,眼光一直追踪那个黑斑。当它逐渐显出一艘油轮的蹲踞形状,接着又显出一艘遣散舰的轮廓时,他高兴极了,惟恐失去它的踪迹,也不等它开近一些,就立即跳进凹坑里去拿那些信号弹。
他放了一个烟雾弹。当橙的浓烟已消散而那艘船仍未改变航线时,他当即又拿起一个照明弹。他把照明弹看成一根巨型洋火,对着那个刮擦平面不停地摩擦。最后它爆出火花时,他便把它投向天空。它飞了一个大弧,还未点着便掉进海里去了。
潘濂又拿起一枚照明弹,他把带子拉开今后,将在弹筒的上端磨擦。忽然嘶地一声发出一道耀眼的白光,接着迸发出无数赤色的星星。潘濂兴奋得大笑起来,心想,此刻那艘汽船一定看得见他了。
信号弹发生了作用,汽船先停止行驶,然后卷起滚滚水花向他开来。潘濂兴奋地向汽船拼死挥手。三个人在舰桥上呈现了,一小群人则靠在栏杆上和炮座上。他瞧见双筒望远镜的闪光,于是他把最后几个信号弹也发射了。
可是那油轮和遣散舰忽然改变了航向,从新消失在天边……
潘濂愣住了。
漫长的飘泊开始了。
由于大部分时间都是坐在水汪汪的凹坑里,潘濂的两只脚、生殖器和脚踝都已肿胀起来。虽然有帆布褥垫,他的脓疮依然不能康复。有一次他掉到海里,身体被筏侧生长的藤壶割伤了多处。一觉醒来,他感受比头一晚躺下睡觉时还要困乏。纵然他已经入睡,恶梦也让他得不到休息。他身心交瘁,思想和目光都陷于含糊,心情亦由希望变为失望。
此刻,潘濂只剩下几块饼干、一点干肉饼和两三品脱水来苟延残喘。必需想措施给自己供给水和食物。潘濂实验在热天多喝水少吃东西,在阴天则少喝水多吃东西。他品味着像砂一样淡而无味的硬饼干,幻想在家里吃面条的滋味。这样的分派好像更公道,大概能够节省水和食物吧。
当然,更重要的是设法增加淡水和食物的量。水好办,下雨时打沸水桶盖接些雨水就足够饮用的了,食物呢?当然,海里有鱼,但没有渔具如何能力抓住它们呢?潘濂想起了那只电筒。他将电筒拧开,把电池取出来,顶住电池的那根弹簧也跟着跳了出来。只要把那根弹簧扭几下,再把它一头磨尖,那就可以做成一个鱼钩了。
今后的很多日子,潘濂都在做以下这些工作:钓鱼,去鳞,开膛,洗鱼,晒鱼,以及把甲板上的鱼鳞和鱼血清理洁净。他的双手由于要做这些洗濯和切割工作,不久就肿了起来,而且裂开了口子。一天要钓捕和晒干五六十条鱼,并且要维修渔具,实在使他筋疲力竭。下雨时他除了汲水,还要洗澡。洗过之后的短暂期间,他会以为嘴里洁净一些,头发和皮肤也不那么黏糊糊了。身体上本来有遮盖的地方,此刻都给晒黑了,皮肤也变粗了。头发长得又长又厚,遮盖了眼睛。
潘濂没有想到,他扔到海里的鱼内脏吸引来了别的凶猛的大鱼。一天,他在钓鱼的时候,感到有东西在拉他的钓丝,可是没有重量。莫非是新来的大鱼把他的鱼饵抢走了。他把鱼丝拉回来,看到鱼钩时不禁大吃一惊,本来那枚鱼钩已拉直了。
从震惊中清醒过来,潘濂意识到自己的鱼钩太小了。动用无法增补的精力,所钓到的只是这样一些小鱼口如果有个能够钓到大鱼的鱼钩,那么一天钓两三条就可以取代他今朝所钓的四五十条了。
他想到了金属。鱼钩必需是金属的才行。他环视木筏。密布于甲板上的已生了锈的钉子怎样?对了,他可以用钉子做个鱼钩。他双手按着甲板,用牙齿咬住钉子使劲地拉。他的牙齿仿佛就将近松脱似的,鲜血从口中流下。他把血吐了出来,然后用较为稳固的臼齿咬住钉子再作尽力。
钉子终于活动了?潘濂不顾牙痛越来越猛烈,仍坚持下去。忽然间,钳住的钉子松了,并且松得很是忽然,乃至他的头部猛然撞向木筏。幸好他牙齿仍紧闭,钉子才没有掉到海里。
潘濂终于制造出了一个坚固尖利的上等鱼钩。
旱季到来了。水源问题成为存亡攸关的大事。
潘濂记得在切鱼时,刀口遇到鱼脊骨就有液体漏出。于是他把一条鱼的脊梁骨破开,吸了脊柱里的液体,使焦干的喉咙轻微好受一点。
随后的那几天,潘濂发现吃生的鱼能使他不像吃鱼干那样口渴。为了增加食物的名堂及膳食中的水分,他还吃鱼的肾、肝和心,并且以为味道很好。一天半夜,有一群密集的鲱鱼从筏下游过,他用两只手捧了上来,整条吃掉。
他的体重已经轻到不能再减的地步,没有肉的肢体被坚硬的甲板碰得遍体鳞伤。三个满月已路过去,什么人的声音也没有听见过,什么人的身体也没有接触过。他的胃液在猛烈地搅动,使他辗转不能入眠。但最后,他仍是因为太倦怠而睡着了。
旱季的风暴也在煎熬着潘濂。滔天的白浪使木筏颠簸得像烈马之背。潘濂从凹坑的一边翻腾到另一边,一面喘息,一面呕吐不已。
创伤和割伤的皮肤很刺痛。可是,此刻他首先得喝水才行。
他用手护着自己的阴部,向着水箱爬去,吃力得使他感到头晕。水箱盖没有想到那么轻易揭开,并且里面的水比他记忆中的还多。他喝了一大口——然后吐了出来。本来水箱里的全部是海水。除非天再下雨,或是他被人救起,不然他就没水喝了。
他爬过适才呕吐出来的污物和腐鱼,辛辛苦苦地把天篷撑好,把水箱倒空。可是精力始终不能恢复。他累得不想吃东西,只能睡觉。
次日,身体僵硬,肚子又饿。但是,他打开食物箱一闻,就知道鱼已经腐坏了。失望之余,他爬到筏边,开始吃力地去撬那些藤壶。他没有当即把藤壶装在鱼钩上面,而是先捡最大几个来吃,让汁液一滴一滴地流下他的咽喉。然后把最后一只藤壶穿在鱼钩上,投下鱼丝。
他急躁地钓了一天的鱼,但是一条也没有钓到。到了傍晚,他把鱼丝拉了上来,索性把那点鱼饵也吃掉……
潘濂也曾遇到一次遇救的时机,但终于没能得救。一天清晨,他瞥见了一架机翼闪着银灰色光芒的飞机,立即跳起身来,从床铺上剪下一块布,沿着一边开了几个洞口,然后把它绑在一只桨上,疯狂地挥舞他那面旌旗。可是,这架飞机终于仍是失去了踪迹……
日子一天天地慢慢过去,潘濂听到的惟一声音,只是海水的飞溅声,以及他胃抽搐时里面气体的咕咕声。他已经七天没有吃东西或喝水了,只能喝自己的尿液。他口干嘴臭,皮肤皱得像个老人。旧创渗出液体,破了的疮疖流脓。他在鱼钩上装上了饵,投下鱼丝,然后闭上眼睛。那天稍后时间,他在险些毫无气力之下,又勉强排出了一罐尿,尿出得很慢,中间曾停顿了多次,并且,它比头一天颜色深,浓度大而分量少。而那辛辣的液体又灼痛了他嘴唇上的口疮。在半昏厥半清醒之间,潘濂瞥见月夜中有只鸟在他头上盘旋。那只黑色的小鸟轻轻地落到木筏上,距离他右手指不到二十厘米。
他抓住鸟的两只脚,把鸟头在甲板上撞了三次。接着,他休息了一会,气喘得很高声,然后撕开鸟的颈部,吸啜它的一点点血液。他倦怠地拉出鸟儿的肠子嚼了又嚼,跟着又吸食它的骨髓,一面吃一面休息打打盹。随后,他取出那乌的心脏、肝和肾,把它们切成柔软湿润的小块,以便他不用嚼就能吞下。
第二天凌晨,他发现海里处处是鱼。虽然钓了两条小鱼之后他已满身乏力,但鱼肉要比小鸟好吃。
鱼和雨的从新呈现使他大感抚慰。看来,最难受的季节过去了。
更令他惊喜的是,他发现海水带有赤色,这说明,他已靠近陆地了。
那天半夜,他高兴得睡不着党。他瞥见在木筏上跳来跳去的鸟类之中,有一只脚爪之间没有蹼的陆地鸟。他弯身到木筏旁边,用手舀了一点水放在嘴里品尝,水的味道是淡的。
朝雾逐渐消失,琥珀色的海洋上现出了蓝绿色的岛屿——由于仍有淡雾覆盖,它们看起来仿佛不是真的。等到淡雾消散后,潘濂瞥见了一只渔船。
“救命呀!”他先用中文然后再用英语喊叫。
此刻距离比较近了,他瞥见那条船其实只是几根粗陋削成而绑在一起的圆木。船上的人是野生番吗?潘濂可以辨出那三个体形——一个男性、一个女性和一个女孩。他们皮肤黝黑,看来不像中国人。
“会说英语吗?”那人喊道。
潘濂惊喜得愣住了。他用手摸了摸他乱七八糟的头发和胡子,然后拼死地又是摇头又是点头地把脑壳乱转一气。
“Chinese。”潘濂把英汉两种语言混在一起,乱七八糟地叫道,“中国人,我是Chinese。”
1943年4月6日,潘濂坐著那条使他得救的简陋的渔船抵达巴西的贝伦港。他在海上飘泊了整整138天——这个记载至今还无人打破。并且,潘濂走上岸时无须别人帮忙。两个月前,就在渔民找到潘濂的那个地方附近,也曾有三个荷兰水手得救:他们只飘泊了83天,但已体衰力竭,濒于灭亡。水师巡逻艇发现他们后,还得把他们抬到船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