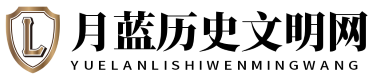天主的谩骂
我的母亲很智慧。她在少女时代就是读着很艰深的课本长大的,后米考上了著名的大学。她人很好,还努力加入志愿者活动,周围的居民都很喜欢她。母亲挺起脊背的那个姿势,就像是在冬季湖面上的仙鹤。她戴着一尘不染的眼镜,透过镜片可以看到她聪慧的双眼。 要说母亲独一的弱点,那就是她分不清宠物猫和仙人掌。不久之前的一天,她把家里养的猫当成仙人掌,用两只手抓住,然后插到花盆里,最后盖上土,浇上水。又有一次,他把仙人掌当成猫,把它拿起来贴近自己的脸,结果脸被弄得处处是伤,还渗出血珠。 父亲和弟弟对于母亲的这种希奇的行为很不理解,就问母亲原由。但智慧的母亲只是站在仙人掌眼前,打开猫食的罐头,对家人的提问充耳不闻。 我很是懊悔,这都足我的错,是我造成的。 从小就有好多人夸我,说我的声音好听。每到盂兰盆节和新年,我们都会去姥姥家,这时候平时极少碰头的亲戚都会围着我。我并不是很善于跟人打交道,仍我会微笑着倾听喝了酒的叔叔们的话,随声附和着,对于听不懂的方言却做出一副很理解的样子。 “你这小孩真是讨人喜欢。” 伯母这样夸我,于是我对她微笑了好一阵子。但实际情形并不是这样的,我的心里其实一直很冷漠,只不过是装出热情的样子而已。 我从来没被亲戚的话打动过,也没有一次为此感到兴奋。不但如此,我还经常以为无聊,想逃得远远的。但我畏惧自己这样做的话,“我”这个股票就会暴跌,围着我转的亲戚会落荒而逃。我并不想把心里的设法表现出来,于是继续装着断别人话的样子,继续说着一些让人以为亲近的话。 当时我心里对自己布满了厌恶,我感受自己就是为了让别人以为我是个好孩子,才装出一脸空洞的笑容,这样的自己真是太浮浅了。 “你的声音很有穿透力,就跟音乐似的。” 一个表姐这样对我说。但在我自己的耳朵听来,我的声音很刺耳,丑恶地扭曲着,就像仿照人类声音的动物一般。 我自己意识到这件事今后,回忆起第一次在自己的声音里注入气力是在小学一年级。那时老师教大家培养牵牛花,所有人的花盆都摆放在校舍旁边的水泥地上。我养的牵牛花长得很大,支棍上缠着绿色的藤蔓,往上舒展着。大大的叶子,叶子上的绒毛结着露水,经阳光一照,薄薄、软软的花瓣就会变成半透明的红紫色。 可是我养的牵牛花并不是班里最好的,班里另有比我的更大、更美丽的牵牛花。 班级第三排的角落坐着一个男生,他跑步跑得很快,名字叫佑一。佑一很是活跃,经常喋喋不休地说着话,并且说话时脸色特别丰硕。我跟他说过不少话,比起谈天的内容,他丰硕的脸色变化更让我以为有趣。他在班里挺有人脉的,我以为原由就在于他那丰硕的脸色。 我想他是存心对我做出那些脸色的,他好像注意到了我想被大家产成好孩子的心情。我很不宁愿,可是他证实了我的阴暗和人性的眇小。那时我自己并没有意识到,我确实对佑一抱着一种不为人知的自卑感。 对于热情地跟我说话的佑一,我老是用幽默的话答复他,这经常引起同学们的大笑。他一有什么感乐趣的事,就顿时想告诉我。可是我的内心从没把他当成密友,我仅仅是做出一些虚假的微笑,对他的搭话做出意想不到的答复。 班里就数佑一养的牵牛花最大最悦目。老师动不动就表彰他的花,而这时我的感受就会很不甘,那种感受就像是体内一只脏兮兮的动物想要钻出皮肤,高声叫出来。而这只动物也就是我的天性。 一天早上,我到学校的时候比平时都早。教师里没有其他人,静偷偷的。这样我就可以轻松地把平时戴在脸上的假面具拿掉了。 我顿时就认出了佑一的牵牛花,它比其他人的要高出一个头。现在佑一的花盆就摆在我眼前,我注视着含苞欲放的花骨朵,往身体里阴暗的地方注入气力,然后念道:“快点枯萎吧!快点糜烂吧!” 我手指牢牢地交叉在一起,绷紧满身的肌肉高声念着,这时我发现鼻子里面有点过失劲,本来是鼻血流出来了。鼻血滴在水泥地上,形成一个个赤色的黑点,就像弄洒了的颜料。 “咔嚓一一”牵牛花的茎折了,上面的花骨朵也掉在了地上,就像人头落地一般。几小时今后,佑一的牵牛花已经枯萎,糜烂了,变成脏兮兮的茶色。 纵然这样佑一也不愿把花弃掉,结果花发出恶臭,招来了好多虫子,不久花盆的泥土上就堆积了大量的蛆。老师决定把那盆花弃掉,于是佑一哭了起来。这样一来我的牵牛花就是班里最好的了。 我的好心情只连续了几十分钟,后来我再也没法看我的牵牛花了,并且就算别人夸我的花,我也只想把耳朵堵起来。 自我从对佑一的花念叨了“咒语”之后,我的牵牛花就成了照出埋没在我身体里的那只丑恶而又恐怖的动物的镜子了。 我念叨了那句话之后,佑一的花就如我所说的那样枯萎了,我不明显这是为什么。但那时的我只是个小学一年级的学生,并没有对我声音里的魔力特别在意。纵然是很气愤的小孩,只要我拼死劝他的话,他也会平静下来。假如我有什么异议,向对方说出来了之后,纵然他是个大人,也会对我这个孩子致歉。 假设有一只蜻蜓停在护栏上,假如你去捉它,它就会灵敏地扇动翅膀飞走。但假如我对着蜻蜒下令说不要动的话,蜻蜓就会像晕倒了一般,再怎么蹬腿扇翅也飞不起来。 我第一次有意识地谩骂就是使牵牛花枯萎那件事,从那今后我开始频繁地向人使用我有魔力的“咒语”。 在我小学快结业的时候,我家附近的人养了一条狗,那条狗总是乱吠乱叫的。它巨大的身体有一半藏在门里边,一有人走过它家的门前,它就像放鞭炮似的不断呼啸。它身上拖着繁重的锁链,但仍旧尽大概地扑向行人,因此铁链深深地卡进它的脖子里,但纵然这样它仍是想咬人。 有一天我走到那家的大门口,狗一发现我,就顿时发出地震般的呼啸,想用叫声来威吓我。这时我说了一句有魔力的话:“不要对着我乱叫!” 结果狗吃了一惊,动了动耳朵,之后就瞪着粘满眼屎的眼睛,不再叫了。 “听我的下令!要听从我!听从!” 我感受到头脑里有火花在飞溅,鼻血从鼻子里流出来,滴到柏油路上。这是我的虚荣心在作怪,我只是想在密友眼前戏弄这条身躯巨大的狗,来获得他们些许的尊敬。 这个愚蠢的筹划很简单就实现了,狗听从我的下令,一会儿抬前腿,一会儿转圈,什么都背做。这件事的结果是我在班级里有了一点名望。 刚开始我还以为很好玩,但后来我逐渐有了一种罪恶感。原来我基本没有勇气驯服动物的,但为了逞英雄却这么做了。这种诱骗他人的罪恶感让我很不安。 愈加希奇的是狗的眼光以前很恐怖,但在听了我的下令之后,眼光不再那么旁若无人了,而是惧怕地看着我。我夺走了狗的斗志,另有它美丽的牙齿。以前那么威猛的狗此刻像只小猫一样看着我,这让我感到它好像在责备我。 我声音的魔力根本是全能的,不过仿佛有几个法则。比方我使用这“咒语”的对象必需是活的生物,植物和昆虫可以,但假如对着石头、塑料发号施令的话,就不会呈现我想要的结果。 别的一旦我使用了这种“咒语”,就再也恢复不到本来的样子了。 有一天我跟母亲发生了一点小摩擦,然后我就对着她说了这样的“咒语”:“你今后再也不能辨别猫和仙人掌了。” 我那时情绪很冲动,基本没意识到自己做了什么。就是因为母亲随便走进我的房间,帮我扫除,结果把我心爱的仙人掌花盆遇到地上摔碎,这让我很气愤。我就是想告诉她我是何等在乎这盆仙人掌,假如用事物在母亲心中的职位来权衡的话,我的仙人掌就相当于母亲很在乎的宠物猫的职位。 母亲错把猫当成仙人掌,往花盆里埋的时候,我心里很是懊悔。我原来应该忍着的,虽然发生了不合自己心意的事,但用有魔力的声音来玩弄他们是恶劣的行为,简直是罪孽深重。我总为这事儿懊悔,但已经迟了。 我想让母亲再次能够辨别猫和仙人掌,于是对她念“咒语”,但母亲再也感受不出猫和仙人掌之间的区别了。 我声音中的魔力不但能对他人的精神起作用,还可以引起身体上的变化。正如我能够让牵牛花枯萎一样,我也可以让动物的身体发生变化。 我上高中今后,仍旧过着向大人谄媚的可怜生活。我无法逃避自己这种糟糕的特性,因为我太怯弱审慎了。我畏惧和别人的关系起任何波涛,老是小心地注意着,不想让自己的身价跌落。在我看来,假如有谁跟我谈天的话,那他就是在观测我,说不定他在会在我看不见的地方偷偷地跟第三人谈论我,讥笑我呢。这简直太恐怖了,所以我做出伪装的微笑。不过最让我以为懊恼的是这种埋没自己本意的做法。 我父亲在大学里当讲师。他的那种性格让我以为他就像一座环境恶劣、严寒、寸草不生的石山。父亲老是居高临下地审视着自己的两个儿子,而我则像是看待天上的神仙那样仰视着他。父亲对所有事情都很严格,自己不满足的东西顿时弃掉。一旦有谁辜负了他的盼望,纵然这个人再次呈现在他眼前,他也会像看待蚊虫那样看都不看一眼。 我背着父亲买了个便携式游戏机。这种游戏机特别小,可以放在掌心,是那种小学生都有的廉价货。父亲平时就对电子游戏抱有不好的印象,他要是发现我买了一个游戏机的话,肯定会特别失望,以为连自己的大儿子竟然都倒戈他,简直想一想都以为恐怖。 弟弟是这样一种人,他会做自己想做的事,想打游戏就去游戏厅,不想学习就把铅笔折断。他这样的人原来就过着跟失望无缘的生活,而我却区别。我为了不让父亲失望,拼死地学习,妆扮得也很朴实,齐整。我这个样子用别人的话来说,就是一个清新阳光的好青年。但这些不过是我的表面,我金色的毛皮下面不过是一团黑乎乎的肉。 有一天,我正在自己的房间里偷偷地打游戏,父亲忽然推门进来了。连门都没敲,他简直像直接闯进犯法现场的警员。他从我手里夺过游戏机,冷冷地俯视着我。 “你竟然做这种事!”父亲用一副不想再管我的口气说道。 父亲看到弟弟加豆谷打游戏已经不在乎了,只当他是个多余的陈设,他已经放弃把自己的第二个儿子培育成符合自己抱负的好孩子了。也正因如此,他对作为哥哥的我抱的盼望尤其大,所以发现我在打游戏后,比我预想的还气愤 假如是平时的我,大概会哭着请求父亲的原谅,但那一刹时,虽然父亲的反感也对我造成了冲击,可我更以为是太没有道理了,为什么弟弟那么自由,我却不能玩游戏?这种感情占据了上风,我感到很生气,竟然就因为我打游戏而否认了我的人品! 等我回过神时,我发现自己正尽力从父亲的手中夺回我的便携式游戏机。我一直都戴着顺从的面具,这是我出生以来第一次抵抗父亲。不过父亲仍旧牢牢地抓着游戏机,不想给我。 于是我在自己的声音中注入魔力,这样说道: “这些手指,掉下来吧!”我和父亲之间的空间被声音震动了,我感到鼻子里的血管绷断了。便携式游戏机掉在地板上,发出一声沉闷的声响。接着父亲左手上的手指齐刷刷地脱离了左手,滚到我的脚下。五根手指齐根断掉了,血从父亲的左手中喷出来,把周围都染红了,也有血从我鼻子里流出来。 父亲发出了疾苦的叫声。但我顿时让他平静下来,下令他,在我说可以之前,不能发出声音。但是父亲虽然发不出声音,他的眼睛睁得老大,盯着自己掉了手指的左手。 我感到作呕,但仍是用力地吸着从自己鼻子里流出的血。我用将近晕厥的大脑思考着自己该怎么办。父亲的手指应该再也回不去了,因为我一旦使用了那种“咒语”,被改变了的东西就再也恢复不到本来的状态了。 没措施,我只好下令父亲:“在我做出提示之前,不要醒过来。”让他临时失去意识。按照以往的经验,我知道我的声音魔力对睡着的人也管用。假如被父亲看着,我就会感到胆怯,不敢用我的“咒语”,所以我让他昏过去,这样操做起来要简单些。 我在父亲的耳边念叨:“左手的伤口赶紧恢复……醒来今后要健忘我房间里发生的一切。”一会儿功夫,父亲的左手以前长着手指的地方就结了一层薄薄的皮肤,于是血止住了。 我必需让父亲以为左手不长手指是很自然的事,并且看到父亲左手的人,也不能以为不自然。 我开始思量,如何能力做到这些呢?我已经能确保让说话的对方发生变化,但我可否让没听到我声音的人也以为不长手指的手是正常的呢? 我下定决心,准备用我的非凡的“声音”说下面的话:“待会儿醒过来后,你看到自己没有长手指的左手,要以为这是自然的状态。并且你的手要让其他看到它的人也以为是正常状态。” 我这种方法不是让没听到我声音的人发生变化,而是对父亲的手发出下令,让手给人自然的印象。 我开始扫除处处是血的房间,用纸巾把父亲掉在地上的手指包起来,放进书桌的抽屉里。父亲的衣服上也有血迹,但我准备对全家人都念“咒语”,让他们不要发现父切身上的血。 我架着父亲走出房间,这时遇到了弟弟加豆谷,他一刹那显得特别惊奇,因为很难看到我架着父亲的局面。弟弟走到我房间里,看到地上躺着的便携式游戏机,于是似笑非笑地看着我。 晚饭的时候,父亲艰难地吃着饭,用没有手指的左手端着碗,但他那种神态很是自然,险些让我健忘了他的手指是怎么掉了的。父亲那没了手指的左手,前端光溜溜的,但在我的眼里就像从小时侯就看惯了似的,大概在家里所有人的眼里都显得很是自然吧。 我发现弟弟加豆谷在偷偷地讥笑我,我知道他这种人以为想讥笑谁就可以讥笑谁,我跟他在同一所高中,差一个年级,我横竖是没措施像他那样生活。 在学校时,弟弟跟密友一起悠闲地在走廊上走来走去。看样子他好像跟密友的关系特别好,而我老是一个人感到特别孤独。我天生就很有心计,老师都是说我常常能制造愉快的氛围,引班里的同学哈哈大笑,但另一方面却从来没有一个人成为我的密友。当然有好多人跟我亲近地说话,大概他们心里都当我是好密友,但在我的意识里,没有人能让我推心置腹,到最后我甚至用生疏的目光端详起我熟悉的人。 我弟弟则区别,他不像我在内心里藏着一只“要在别人眼前表现好”的动物,他大概只是很自然地把心里话讲给好密友听,在这一点上他比我要健康得多。 可是难以想象的是,在世人眼中好像我要比弟弟要好,这是由于我脸上老是戴着顺从的面具。假如弟弟在我眼前感到自卑的话,那就相当于我对他做了很过度的事。为此我想对加豆谷致歉,但我跟他之间不是那种什么话都能说的关系。 原由在我,这是因为他发现了我内心丑恶的设法,知道我的浮浅,我老是听爹妈的话,尽力得高分,获取周围人的信任。因此他以为我跟他说话也是件不洁净的事,看我就像看一件肮脏的东西,老是在无声地责备我。每次就在我想要奉承一个人,找到了一个让我定心的地方时,假如他恰好从我身边走过,我正好遇见他藐视的眼光,他正在讥笑我风趣的样子,我就会一下子感受天崩地裂,所有的声音都冲击着我的耳膜。 学校的自动售货机前面,正有几个学生在妙语横生,他们并不是想买什么饮料,是在那儿闲谈,我想从自动售货机里买点东西,但又不想穿过人群,只能站在附近等他们到另外地方去。这是因为假如我向他们提出要求,让他们移一下的话,他们会给我让个地方,但假如他们为此不兴奋的话,那怎么办?我内心的设法就是这样。 这时加豆谷来了,他毫不迟疑地推开自动售货机前的几个人,把硬币投入机械里,他手里拿着罐装饮料的时候发现了我。他好像看穿了我为什么在那里站着,于是留下一个意味深长的微笑,然后扬长而去。 加豆谷果真知道了我的机密,他知道他的哥哥很受欢迎,别人都以为他待人接物的立场很好,是个很当真的人,但实际上这些都是假象。他知道我为了让别人喜欢我,强颜欢笑,肤浅至极,小心到甚至连跟自动售货机前的几个学生说话的勇气都没有。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不管在家仍是在学校,跟弟弟加豆谷擦肩而过的时候我老是渗出一身的汗。我对知道我天性的加豆谷感到畏惧,在他眼里我大概不是他的哥哥,而是一个让他看不起,让他想吐唾沫的家伙。 我一般极少有时机跟加豆谷说话,但早饭时一跟他坐到同一张桌子上,我的胃顿时就以为很疾苦。我好像要被他轻视的目光羞得无地自容,手心里都是汗,连筷子都拿不好了。但就算这样,我仍是要装着很兴奋的样子,微笑着跟爹妈亲说话,津津有味地吃着饭菜。这样的生活我过了太长时间,此刻吃点饭就想吐出来。 晚上我也睡不着,老是翻来覆去的。我不再做一些轻松的梦,一闭上眼睛,面前就会浮现出好几个人的脸孔。他们都像弟弟那样轻视地俯视着我,而我则叩首如捣蒜地给他们谢罪。有时候我醒着,也会以为房间里处处都是眼睛,都在指责我。这种时候我真的情愿死掉。 是不是这个世界上只有我一个人的话,就不会那么疾苦了呢?被别人讨厌,被别人看不起,对我来说是难以忍受的疾苦。于是为了逃避那些,我在自己的内心养了这样一只丑恶的动物。假如没有别人在这个世界上,就只有我一人,那将是何等轻松啊! 不,我是不能忍受别人看到我,我不能接受别人看到我今后发出苦笑或者做出失望的样子。于是我思考如何能让世界上的人都看不到我。 我准备先对恣意一个看到我的人说这样的咒语:“一分钟今后我的形象将在你的眼睛里消失。”然后接下来再使用这样的咒语:“你的眼睛看不到我今后,你要把我对你说的咒语感染给所有与你对视的人。” 我的策划也就是借助声音的魔力,使第一个永远看不到我的人,在与第二个人对视的时候,我的形象会同样从第二个人的视线中消失。第二个人再与别的一个人对视的话,这第三个人的视网膜上也会无法出现出我的形象。这种情形会重复发生,我的透明度就会增加。假如全世界的人都看不到我的话,我就成了完蛋全全的透明人了,这样我就应该可以永远安心了吧。 不过在这之前我得处理一个问题,这就是把自己从“看不到我”这个链条中除去,不然我照镜子的时候,自己都看不到自己了。 有一天晚上,狗死了,就是我上小学的时候为了自己那点无聊的虚荣心而加了“咒语”的那条狗。我一直都定心不下那条狗,它每次看到我都很是畏惧。 我从爹妈那儿据说狗死了的消息,顿时去养狗的那人家里。又大又威猛的狗躺在水泥底上,一动不动。我抱着它,哭了出来。不知怎的,我感到很是哀痛。细心的主人脱离了,让我和狗单独待在一起。 我用尽满身的气力,从腹腔底部发出颤动的声音,下令狗道:“快点给我活过来!”可是狗并没有活过来,只有掉在地上的一撮一撮的毛在夜色中飞翔着。我能够为了自己的一点表现欲而对狗使用“咒语”,却不能让它再活过来。 不但如此,我以为自己此刻想让狗活过来也不是真的对狗的死感到伤心,我只是想尽大概地减轻自己的罪过而已。 我又看了一眼狗的脸,发现它仿佛终于放下了所有的重担一样,宁静地闭着双眼。我有点羡慕它了,它死了,同时也获得了摆脱。 有一天半夜,当我回过神来的时候,发现自己正站在房间中央哭着,手里拿着一把镌刻刀。我满身都是汗,一直在那儿不断地反复着“对不起”。我大概正准备割自己的手腕,不过忽然醒了过来。我看了一眼木制的书桌,上面有一道镌刻刀划过的陈迹,桌子脚下有一些卷起的木屑。我想仔细观测一下桌子,于是把脸凑近,发现桌子里有一股糜烂的恶臭。 我打开桌子的抽屉一看,卷起来的面巾纸里包着五根糜烂的手指。每根手指都发黑了,应该在抽屉里放了很长时间。但我看得手指上稀疏的汗毛时,我想起来这本来是父亲的手指。那时我不知道怎么处置房间里的手指,于是放进了抽屉里,不过这些事我已经忘了。我让自己以为父亲的左手没有手指是理所当然的事,同时放在抽屉里的手指也顿时从我的记忆里消失了。 我把开始糜烂的手指埋到院子里,埋得很深。但在那之后,从桌子里发出来的糜烂味道并没有消失,而是在一天天加强。那种感受好像是抽屉跟另一个世界毗连在一起,糜烂的味道从那个世界的漆黑中源源不停地飘来。 不久之后,桌子上的划痕又增加了,刚开始只有一道,几天今后就成了两道,几周今后桌子上已经靠近十道划痕。 吃早饭时,我感受给我做早饭的母亲和用左手压着报纸的父亲不是人,而是一些会动的木偶。在上学的途中,检查我月票的人,坐在我旁边的人,在学校和我擦肩而过的人,在我眼里都不是生物。我感受他们不会思考,他们的皮肤被设计得很精良,但里面都是人工制造的部件。 但我为了让他们不丢弃我,仍旧对他们报以笑脸。我脸上越是挤出畅亮的笑容,我的心灵越是变得荒凉,而我越来越畏惧弟弟,我听不到其他人的呼吸声了,但他的影象却越来越清楚。 加豆谷并没有亲口说出来,可是他嘴边露出的冷笑,肯定是针对我好笑的人品的。他的冷笑就像鬼魂一样跟在我身边,不断地指责我,让我很是苦恼。这个时候,假如周围没有人的话,我为了让自己安静下来,会用头去撞墙,有好几回都是这样。最重要的不是弟弟太可恶了,而是我自己原谅不了自己。 但我仍旧以为让我疾苦的元凶就是加豆谷,这就是我想杀他的原由。 我按下盒式录音机的停止键,把磁带倒回到开头。我回味了适才听到的内容后,身体不由得不断地颤动。我的视线由于泪水而变得含糊了,在我含糊的视线里,我往镌刻刀里倾入气力,在桌子上划了一道陈迹。这样桌子上的划痕又增加了一道。 我身上流着汗,对闻到的恶臭皱着眉头。我开始想象:窗外无边无际的无声世界,咆哮的暴风带来的腐臭,细菌让肉糜烂掉,发出恶臭,然后把肉烂光了。 我的心里涌起一种感情,无法抑制,于是我坐在床沿上,把脸埋在胳膊里哭了起来,这时我手里仍旧拿着那把镌刻刀。 等我醒过来的时候,我发现自己正握着镌刻刀坐在床沿上。手一松,就像丢掉一只毛毛虫那样,于是镌刻刀掉到了地板上。我一看桌子表面,发现不知不觉间又多了一道划痕,划痕的数目已经跨越了二十。 大概是我自己划的吧,不过我并没有这样的记忆。 我感到自己忘了一件很可怕、很重要的事情,于是心情变得不好起来。我以为自己的记忆仿佛被谁动了手脚。在不安中我低头看了看地上的镌刻刀,在它的尖端我感受到了一种让人发疯的妖气。 晚饭之后,弟弟加豆谷斜躺在起居室的地毯上,正在看棒球角逐的转播。他一只手支着头,另一只手在拿着果子吃。 杀了他吧,我含糊地想道。我躲在自己的房间,等候深夜的到来。桌子里仍旧飘着恶臭,就像把宠物的尸体放在了抽屉的深处。 我告诉自己,要杀掉弟弟这件事不能有丝毫的踌躇。不杀了他的话,我自己就要完了。他那看穿了我天性的眼光穿过我的皮肉,他嘴角的讥笑一刻也没有脱离我的耳膜。 为了能安稳地生活下去,我必需从这两个方法中选择一个:一个是我自己去一个没有任何人的世界,另一个就是让加豆谷从我的世界中消失。 几小时过去了,时钟的指针已经指向了深夜。我从自己的房间走了出来,向弟弟的房间走去。走到他房间的门前时,走廊的灯光将我的影子投在了我的眼前。看到自己的影子仍旧是人的形状,我的心情有些复杂。 我把耳朵贴在门上,确认他正在熟睡之后,我的手握住冰凉的门把手,打开了一条缝。我屏住呼吸,溜进房间。房间里很是暗,不过我没有开灯,只是借助走廊的灯来窥伺。 我看到弟弟床上的被子隆起一块,知道他就在床上。我偷偷地走近床,低头看着熟睡的弟弟。门口透进来的光被我的身体盖住了,在我弟弟的脸上投下了影子。我把嘴接近他的耳朵,想对他念一些关于死的“咒语”。 就在这时,弟弟翻了个身,床发出“吱呀”的一声。他发出一声低低的,好像从睡眠深处醒了过来,然后他的眼睛睁开了。 他看了看打开的房门,最后才发现站在床边的我:“哥,怎么了?” 他轻微歪着头,亲近地对我说道。我双手掐住加豆谷脖子,他像女孩般瘦弱的肩膀由于惊奇而耸了起来。 我用尽满身气力说道:“你给我去死吧!” 加豆谷纤细的手指伸向空中,好像想向人求救,他的眼里布满了惧怕。可是我发现有点过失劲。每次我使用“咒语”的时候,鼻腔的深处都能感到一个小小的爆炸,但这次却没有,也没有血从鼻子里流出来。 我把手从弟弟的脖子上收回来,这时难以想象的是他竟然也没有咳嗽,也没有质问我,就像做了一个梦一样,又若无其事地闭上了眼睛。他的样子跟平时没什么两样,这让我感到很过失劲。我走出他的房间时,转头一看,他已经宁静地睡着了。 “啪”的一声,我的脑壳里像爆炸了一般,我像被上了发条一样顿时跑回自己的房间。我向桌子上一看,发现之前一直没注意到的盒式录音机,旁边堆了一堆备用的电池。录音机的插头并没有插上,仿佛是里面的电池驱动的。我不应该一直注意不到这些东西的,我一直都没发现它的存在,这是一件很不正常的事。 盒式录音机里面放了一盘磁带,我不知道为什么,以为自己必需从新放一遍磁带的内容。我的大脑里仿佛被下了这样的下令,于是手指自动地按了从新播放的按钮,动作连自己都无法控制。 从透明的塑料窗口里可以看到开始旋转的磁带,接下来扬声器里传出来的是我自己由于紧张而颤动的声音: “事情变得复杂起来了。这盘磁带已经播放几遍了?此刻的我很难想象。听着磁带的你,大概就是几天今后,或者几年今后的我吧。 总之让磁带从新播放的你,肯定已经忘了发生了什么吧。我把一些必需的‘咒语’录进这盘磁带里的话,就可以把一切都忘掉,过着一如既往的生活。 我准备这盘磁带的目标就是这个,我想在未来的自己听一听自己曾经都做过些什么。 你大概会顿时以为必需让这盘磁带从新播放一遍吧,这也很正常,因为我在磁带的末了录入了这样一段有魔力的咒语: ‘想杀某个人,或者想的时候,你将在桌子上发现一个一直没注意到的盒式录音机,然后你回忆从新播放一遍里面的磁带。’ 听着这盘磁带的你,大概想杀掉某个人,或者在想用什么方法来,这个我无法判定。 可是我必需告诉你一个道理,也就是说你基本没有必要杀死某个人或者。理由很是简单,因为跟你一起生活的所有人都已经不能动了。父亲,母亲,弟弟,班上的同学,老师,另有那些没见过的人,他们都已经不在这个世界上了。残留在这个地球上的,大概只有囊括你在内的极少的人。 我以前思量过这个问题,假如我的形象在世界上所有的眼里都出现不出来了,那我该怎么办,你还记得这件事吧。 那条狗死了的第二天早上,我仍旧像往常那样装出丑恶的笑容,坐在桌子旁吃我的早餐。这时加豆谷揉着眼睛起来了,母亲拿了一盘煎鸡蛋从他眼前走过。父亲正皱着眉头读报纸,他翻过一页的时候,报纸的一端正好遇到了坐在旁边的我的胳膊上。打开的电视里正放着广告,我忽然感到自己受不了了,想杀了所有人。 也就是说我用了这样的咒语: ‘一个小时今后,你们的头将从脖子上掉下来。’ 接着我又下了这样的下令: ‘你们滚到地上的头,把对你们施加的咒语感染给所有看到你们的人。’ 当然我附加了把我自己解除在咒语之外的话,同时还对他们的记忆动了手脚。也就是说他们会忘了听过我的咒语,然后脱离家。 在我对家人施加了咒语的一小时之后,我正在学校。这时加豆谷所在的班级一片混乱,我去看了看,发现弟弟的头掉在地板上,学生和老师们围在血泊四周,表情煞白。 这是一个有魔力的头,看到它的人一个小时之后,就会死去。我推研发出尖叫的人群,脱离了那边。这时父亲和母亲的周围肯定也发生了同样的情形。 又一个小时过去了。在堆积到学校的警车和周围居民的眼前,曾看过加豆谷滚到地上的头的几十个人,他们的头也一起骨碌碌地滚到地上。连一声尖叫都没听到,忽然之间就有一堆头掉到了地上。 这时数目是适才一百倍的人目击了这个场景。 很多人都陷入了惊恐和混乱之中,这时电视节目标摄像机也来到了现场,他们直播了这些一个小时今后将宣告灭亡的头颅。这一刹时我的咒语将通过电波感染,最终将取下无数人的头。 那天薄暮,街上静偷偷的,沉寂的空气里落日投下长长的影子。我走在一片血红的街上,无数的人静静地躺在地上。希奇的是我的咒语仿佛对动物和昆虫也起作用了,地上处处都是没有头的猫呀狗呀蟑螂苍扼等等。 仿佛好多地方发生了交通事故,可以看到好多地方冒着黑色的烟。绝大多半的电视里什么也没播放,我偶然会看到没有头的新闻播报员趴在桌子上。 不久街上的灯都熄灭了,大概发电站没有操做的人了,最终没措施正常供电了,全世界应该都发生了这样的情形吧。 我在确信世界上除了我没有其他生物活着之后,一个人走在暗淡的街道上。不管走到哪儿,地上的柏油路都是脏的。 我看到撞在一起,冒着黑烟的车,车的驾驶席上坐着一个脑壳连在身上,一动不动的人。他大概是在看到某个掉在地上的头之前就死于交通事故了吧。 静静的夜空现出了点点繁星,我坐在过街天桥上仰望着星空。希奇的是她到来之前我一直没有受到良知的指责。 我正在仰望星空的时候,听到了莱个地方传来很轻的脚步声,另有告急的声音。我从天桥上往下一看,有一辆由于交通事故而正在燃烧的车,在火焰的照耀下,有一个年青的女性在颤巍巍地走着。我感到难以想象,就向她喊了一声。 她听到久违的生命的声音,脸上露出定心的脸色,然后把脸转向我的方向。 一刹那我就明白她的头为什么没有掉了,本来她是个 瞎子,眼睛看不见。 她的命运真是太差了。我满身战栗,然后从那个地方逃走了。我的心里涌起了排山倒海的罪恶感,可是这个世界已经回不到过去了。 有很长时间我一直很疾苦,我看到世界上处处都是糜烂的人,感受自己受不了这个世界了。 于是我决定忘掉这一切。我要让自己产生错觉,让自己忽略此刻的状况,健忘被灭亡覆盖的大地,继续活在之前的世界里。我决定在这盘磁 带的最后录上这样的咒语:‘你每次用镌刻刀在桌子上划上一道痕,你就会以为自己正生活在过去的正常世界里。虽然实际上你只是在吃着食物,睡觉,保持健康,维持生命活动,但这些不影响你的意识,你要以为自己还和从前过着一样的生活。’ 顺便我还思量到把自己房间里的桌子解除在前提.之外,我下了这样的咒语:‘你的幻觉影响不了这张桌子。’也就是说纵然我过着跟以前相同的生活,但我的桌子是跟现实世界连起来的。 你听到这盘磁带,是不是正在懊悔?你大概会想再次把这一切都忘掉,从新回到听磁带之前的自己吧。假如是这样的话,你只要再在桌子上划上一道痕就可以了。 桌子并不是你的幻觉,因此可以通过你的划痕来记实你听着磁带洗去自己记忆的次数。 此刻桌子上有几许道划痕了呢?” 在这之后磁带另有独白。过去的我仿佛通过磁带来对自己下咒,来对自己的记忆进行操做。我把脸凑近桌子,闻了闻臭味。从镌刻刀划的一道道伤痕,或者是从抽屉的深处,传来异样而又潮湿的腐臭。对面的现实世界,通过桌子的抽屉,只有臭味飘到我见到的幻觉世界。 我坐在床的一端开始想象。在腐肉组成的世界里,只有我一个人穿戴校服去上学。走到没有人的检票口,我举着月票,来表明自己不是非法搭车。我坐在摇晃的电车里,走着相同的路线去学校。我踏在地上各种各样柔软的东西上,悄悄地穿过校门。为了不让人以为讨厌,我做着假笑走进没有扫除的课堂。我在课堂里做了一个梦,梦到班里的同学吵吵嚷嚷的,然后老师很气愤,下令大家平静。但实际情形是我一直坐在沉寂的课堂里,坐在自己的座位上。我头发蓬乱,眼神空洞,就是这样仍是拼死地装出笑脸。我这个样子更像动物,而不是人。 有人敲我的房门,我应了一声,接着抱着仙人掌的母亲打开了房门。 “你还没睡吗?快点睡觉!”母亲面无脸色地说道。 这个世界上只剩下我一个人了。想到这里,我的心理涌起一种情感,无法抑制。 “你的手在擦眼泪,你哭了,到底怎么了?身体不惬意吗?” 我摇了摇头,我哭并不是因为身体不惬意,而是感到定心了。我终于来到了求之不得的一个人的世界了,我的心终于安静下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