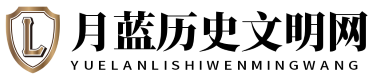剪发尸
四周静谧得很诡异,阴冷的月光柔柔地洒在川原惊骇的脸上。突然,川原一直抿着的嘴微微张开,露出一副让人胆寒的笑容,细声细语道:“本来你基本没有眼睛。” 1、序幕 川原在一场大病花光了自己所有的储蓄后,就在一处平时不太会有人惠顾的地界低价租了一间铺子,做起了帮人剪发的交易。 近几天的交易比过去愈加昏暗了,无奈的川原只好利用延长开店时间来吸引更多的客人,有好几回,川原都红着眼把店开到了半夜十二点。 由于这片地方是旧区,所以人并不是好多,这附近大多住着老人,他们的孩子只有等到双休日时,才会来看他们,把他们带到川原的店里来,川原的交易只有到当时候才会稍稍好一点。那些老人有些个比较迷信,没事就喜欢在川原的店里说些妖狐鬼魅之类的奇谈,有时也把川原唬得一愣一愣的。 前些日子,在离这儿不远的德云镇上发生了一起耸人听闻的,一位狠心的儿媳因为受不了持久照顾双腿有残疾的婆婆,竟狠心将她推入井中,活活淹死。据来剪发的福伯所述,那具尸体刚从井里打捞出来时,景象万分可怕!尸体的那张脸就犹如宣纸一般惨白,一双充着血丝的眼睛,恰似要迸裂开来,抱怨地看着世间的一切。不过这还不算最可怕的,福伯在瞥见尸体后的第二天,到公寓附近的公园晨练时,刚巧听见一位在石凳上打牌的计程车司机,如此这般地描述了自己昨晚在命案现场敖近的见鬼经历:“或许是早晨一点左右,我送完最后一位客人,正准备往家里赶,行到一处小路时,我猛地记起今早发现尸体的地方就是这条小路尽头的那口枯井里,虽然平时自己都是走这条路回家的,可今儿不知怎么的就踌躇了,合法我拿不定主意之时,面前竟然呈现了一个人影,我定睛一看,你猜我瞥见了什么,是那个老太婆的鬼魂啊!只见她神色肃穆,两只手扶着轮椅,一颗头晃晃荡悠的,眼睛笔挺地看着前方,真的是太恐怖了!” 只管这位司机讲得栩栩如生,可仍有一些人提出了质疑,可希奇的是,那些有关鬼魂的传言却并没有因此而停止,反而愈演愈烈,后来人们甚至说老太婆的身后呈现了一位推轮椅的老伯,而那个人就是老太婆的老公。至此关于她老公的流言蜚语众说纷纭,有人说老人在很早以前就已经病逝了,也有人说老人去了一个地方今后就再也没有回来,但是事实上谁也没有真正见过老太婆的先生。大概只有这样不断地制造话题能力真正填补人类的好奇心,为原本枯燥乏味的生活洒些不一样的调味剂。 福伯临走时听人说川原近几天都把店开到很晚,出于美意,便对川原提醒再三,川原笑着说了好几声“是”。不过福伯接下来要说的事,却让川原有些笑不出来。福伯依附着自己多年对命相一说的深研,他算出川原近日必有一场大劫,并且与钱有关。他送了川原一只黑不溜秋的老猫,根据福伯的说法,这只老猫拥有些许灵力,大概能帮川原降住一些东西。川原实在拗他不过,只好答应把猫放在店里照顾几天。 那天晚上苍阴得吓人,可却不像要下雨的意思。黑暗的行人道上空无一人,川原一看挂钟,时间竟还不到夜间十点。一般的时候,夜间十二点,行人道上都不至于半个人影也见不着。这种情形下,川原的店里当然更是冷静,无聊的川原坐在椅子上竟睡着了。 时间不知过了多久,巷口的那几只疯狗突然狂叫起来,川原一惊,立即醒了过来,一睁眼,就看到上午福伯送给他的那只黑猫正睁着它绿幽幽的大眼睛,哀怨地盯着自己。 川原愤怒地喊了一声“走开”,把它从桌上赶了下去。看墙上的挂钟,川原有些不敢相信,已经深夜一点了!莫非自己睡了近四个小时? “有没有搞错,到底是谁家养的疯狗?”川原一边埋怨,一边打开店门,想看看街角究竟发生了什么,面前的一幕却让他的心禁不住凉了半截。 2、惊魂 在一片浓稠的夜色之中,一个坐在轮椅上的老太婆从店里透出的光晕中缓缓呈现。她的脸惨白极了,不见一丝血色。嘴微微张着,像是想向谁说些什么,可希奇的是,那两片已经变成暗紫色的嘴唇竟察觉不出一丝抽搐,很清楚,她的嘴已不知什么原由僵住了,像死尸一样,一双充满血丝的大眼睛更是慑人,黑色的眼球如同被下了咒般,突兀地悬挂在眼睑下,一动不动。 妇人后头还站着一位推轮椅的老者,头发斑白,戴着黑色边框的老花镜,面上没有任何脸色,腰板挺得笔挺,瘦小的身段活像一具干尸,一具会走、会推轮椅的干尸。 莫非福伯的鬼话真的应验了?他们就是德云镇上的那对年老的鬼伴侣?可假如然是德云镇上的鬼,为什么会在这里呈现?难道我真有一场大劫?!川原越想越畏惧,他活了这么久,但是连个鬼影都没见过。 很快老者停下了轮椅,欲推门进店,呆立在原地的川原情急智生,说道:“对不起,先生,我想我的店铺大概要关门了,不如明天请早。” 老者的脸一点一点地变暗:“我们两位老人家腿脚不利便,找了好几条街,就你这一间剪发店有灯光,你就不能行个利便吗?”“但是……我……”川原一脸的踌躇。 “小师傅,理颗头不会耽误你太多时间的。”老者神色异样地说道。 川原本想再说点什么,可无意间看到老太婆那双从未眨巴过的眼睛正直勾勾地盯着自己,心脏马上一阵狂跳。强压之下,只得将两位请进店来,此时的他只想把这最后的一单子交易快点结束,好送走这对麻烦的客人。 “请问是哪位要剪发?”川原有礼貌地问道。 “是我的老婆。”老者将轮椅上的老太婆推到剪发镜前时,说道。 “那把她抱到这张椅子上吧。” “小伙子,能搭把手吗?”老者冷冷地问道。 “好的。”川原说完用手托住了老太婆的腋下,可刚一接近她的身体,心便禁不住一颤,她的身体竟如冰柱一般冰冷! “她的身体?”川原错愕地看着老者。 “没事的。只是一般性血虚罢了。” “血虚只会使手脚冰凉,并不会使整个身体都向外透着冷气。”老人显得有些不耐烦,说道:“我老伴的身体在我脱离之前就已经是这样的了。” “脱离?脱离哪儿?德云镇吗?” “你怎么知道?” “我、我只是随便猜猜的。”川原的语气小心了好多。 “想怎么剪?”川原只管一肚子的问号,可依然不敢怠慢。 “剪短就可以了。”老人在身后找了张靠背椅坐下,心不在焉地答复道。 川原如平时一样,先从推拿主顾的头皮开始。他的手指微微分隔,当梳子用,慢慢地捋着老太婆的头发。头发很稠密,不过有些干燥,但这一点儿也掩盖不了发质的无瑕,假如仅从这一头光明舒柔的黑发来遐想,完全无法与面前这位老太婆的苍老容颜联络起来。 推拿的时间稍稍短了点,并且手法也显得颇有点儿缓慢。只因此时的川原实在没有措施集中工作时的十二分精神,只管他已经很尽力地让自己进入到一个剪发师的角色,可每次都会因为一个恐怖的疑问,而莫名其妙地从工作状态中摆脱出来。 那个疑问是——我在理的是一个死人吗? 3、黑猫 镜子里反射着老太婆恐慌万状的脸,好像一面精心镌刻的面具,但最令川原以为不寒而栗的是,老太婆的身体从呈现以来就一直保持着同一个姿势,四肢如被冻住,眼皮也不见她眨一下,真正像极了香港电影里的僵尸。不过她要真只是具尸体还好,川原最怕的是今夜冷不防应验了福伯早上的忠告——自己将有场大劫。 突然一声猫的轻唤冻结了川原惴惴不安的心绪,声音是从洗手间传来的,哀婉而悲凉,似远嫁女梦里的哭诉,又如未亡人坟前的低吟。川原恍然记起今晨福伯寄养在自己店里的那只黑猫,刚才还不见它的影踪,本来是躲进了又脏又乱的洗手间。 “你、你听到猫的叫声了吗?”老者的声音在打颤,表情发白,感受被一种不可言状的可怕所覆盖,“你的店里有养猫吗?我刚才进店时仿佛并没有见到!” 也许是老者的声量太小,川原并无留神到老者语调里的不安,只道:“是一位老顾客寄养在我这儿的。” 话音刚落,川原即从眼角看见那只黑猫正往老者的方向缓缓踱去,迈着轻盈的步履,娇小的身姿迟缓地摆着。 黑猫挪至离老者两米不及的地方就停了下来,两只绿幽幽的眼睛泛着冷光,哀怨地瞅着好像有些坐立难安的老者。 “快走开!”老者情绪冲动地冲那只黑猫喊了一句,但这招好像起不了一点儿作用,那只黑猫仍然静静地站在原地,无论是姿势仍是视线都无任何改变。 老者一下子慌了,坐也不是,站也不是,双腿不由得瑟瑟发抖,沿眉心滴落的汗水一点一点含糊了他本已不太清楚的视线。 “您没事吧?”川原从剪发镜里留意到老者的神情过失,问道。“没、没事。”老者有意粉饰自己的慌张,把说话时的语调尽大概压低,可是拘泥的口气仍使他的不安袒露无遗。 川原困惑地瞅了老者一眼,跟着把眼光迁至黑猫的身上,突然,一个不甚确定的动机在他的脑海里闪过——那只黑猫的呈现让老者感到畏惧! 从进门一来,老者的眼神与语气一直保持冰凉,可是自从那只黑猫呈现后,一切好像都起了变化,老者不再如刚才那样安静,相反的,他的脸上更多浮出的是不安与烦躁。莫非那只黑猫真的是福伯所说的灵物,可以助人驱病挡灾,必要时还能用来唬退游荡在阳间的阴灵! 老者终于坐不住了,起身朝川原走去,冷冰冰地说:“我想,我们该走了。” 川原呐呐地说:“可、可我还没有帮您的老婆理好头发。” “不用了。”老者的立场强硬,不容川原有半点迟疑。 诚实说,川原的心里还巴不得把他们送走,只是无奈没有合适的理由,此刻老者自己提出了想要脱离的要求,川原岂有不承诺的道理,但面上仍是要装成一副为难的样子,道:“其实头发已经剪得差不多,回家只要清洗一下就可以了。” “几许钱?”老者冷冷道。 “不用了。”川原并非故作客套,他着实不想要老者的钱,原由很简单,那种感受怪怪的,就仿佛向死人要钱。 老者愣了愣,道:“不行!钱仍是要给的。”说完,他即把手伸入裤袋,慢慢探索着。 川原极力抑制着自己过激的呼吸,充血的眼睛死死地盯着老者的那只手。川原真怕他掏出一张冥币。不过,幸而事情并没有往更恐怖的方向发展,老者掏出的是一张崭新的一百元钞票。 川原心有余悸地接过那张一百元,胡乱放入自己的口袋,并匆忙匆忙找了九十三元给老者。 老者拿过钱,看也没看川原一眼,低着头把老太婆从剪发椅上抱下,然后用心整了整她的衣裳,拉开老式的店门,推着车缓缓走入夜幕之中。 那晚之后,川原满心觉得不会再有什么怪事发生,可谁料到,一则毫无噱头可言的法制新闻就把他这个近乎天真的设法逼进了死角。新闻是关于那对老汉妇的。 4、 川原看到那则新闻是在三天后的晨报上,那时他正在给一位两鬓花白的老顾客推拿头皮,见福伯一脸繁重地走了进来,手里还拿着一份刚从书摊上买来的晨报。 “唉!怎么会出这种事呢?”福伯一坐下就在那儿长吁短叹。 “怎么了?”川原知道假如自己不立即接下话茬,福伯一定会自顾自地喋喋不休起来。 “你没看今天的晨报吗?前些日子闹得沸沸扬扬的‘德云镇闹鬼事件’被证实只是一出闹剧。” “闹剧?!”川原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福伯伸手把那份晨报递到川原面前,并用食指点着其中两张好坏的脸部特写照。 照片虽然登得很含糊,但川原仍然一眼就认出来,他们即是三天前呈现在自己店里的那对老汉妇。川原登时傻了眼。 本来那对老汉妇过去在片场堡作,男的是化装师助理,女的则是一名暂时演员。几年前,他们因为年纪过大而双双下岗了。回到德云镇后,他们的生活过得十分窘迫,伴侣俩膝下无子,在德云镇也没什么亲戚,平时深居简出,与人无争,但这份始终维持不易的均衡还是给一场风浪打破了。一个月前,老太婆莫名其妙地患上一种怪病,后经就诊,是一种稀有的遗传病,患者最突出的病症就是满身冰寒,发病时下肢僵直,无法行走。 由于这种遗传病一般都会在人年入花甲之后才显露出来,所以治愈的机率并不太大,不过假如稍加调理,可以减轻发病时的疼痛,但调理用的药却不廉价,在一千元上下。这无疑给老两口原本就不富足的生活负上一笔重担,正在他俩犯难之际,邻居李麻子告诉了他们一条生财之道。 李麻子生了一张远近驰名的麻脸,打小没干过一件功德事,十九岁那年还因为偷携毒品被送入牢狱关了两年。前些日子,李麻子也不知是从哪儿弄来了几千张一百元面值的假币。就做工精度而言,李麻子找来的那些假币做工广泛粗拙,骗骗老人还行,万一让哪个眼尖的知识青年撞见,不免原形毕露,况且几千张的数额也不算少,假如用得太频繁,少不了有人发现。所以他就寻思着找些不识货的人卖掉一部分。好巧不巧,老汉妇就成了他觅得的头一个目的。 那天晚上,李麻子主动来找配偶俩,一进门便开始滔滔不绝地推荐起那些来源不明的,老太婆一开始并不想承诺,可看到老先生的神情正给李麻子说得越来越坚定,心头的那份顾虑也禁不住流散了。老先生在李麻子苦口婆心的奉劝下,心一横,用仅剩的那点儿储蓄购置了十三张一百元面额的假币。 伴侣俩盘算着假如十三张假币全花掉,一千元的药费就有着落了,可怎样花掉是个问题!无计可施之际,不知是巧仍是不巧,德云镇发生了一件“大事”。先是有人声称半夜撞鬼,后又有街市之徒请人作法,一时之间弄得满城风雨,人人自危。 世上鬼魅灵异之事千种万种,怕的人越多,信的人越多。 老先生不由计上心头。此妙计不仅能容易把那十三张假币花掉,并且还不会让他与老婆负上半点儿责任,只是如此难以想象的绝佳好计,却有个不是太雅的大名——“装鬼”。 老先生过去在片场只是一名化装师助理,但是要说到老太婆的演技那是最令老先生定心的,老先生从熟悉她的那会儿起,就一直相信她是位很有潜力的女演员,怪只怪时运不佳,老太婆年青时演的多半是些小氨角,不好听地说,其实就是一名暂时演员。 老先生思量再三,决心把筹划实施地定在川原现居的那个小县。一来那个小县离德云镇较近,因为假如直接在德云镇上“扮鬼”,恐让熟人撞破。二来有关德云镇的“闹鬼惊谈”早已把那边弄得胆战心惊。老先生可谓占尽“天时、地利、人和”,想不成功都难。 接下来就犹如列位在小说前几部分里看到的那样,老先生充分揭示了自己的演出能力,利用人恐惧“鬼”的心理,成功从川原那儿用一张一百元的换取了零头,当然这其间老太婆毫无马脚的演出也为这场圈套注入胜算的筹码。 只是百密终有一疏,老先生忽略了一样有大概让他的筹划付诸流水的偶尔性因素,那就是猫。 其实老太婆除了患有满身发寒的遗传病外,还得有稍微的猫毛过敏症,过敏反映囊括抽鼻子、打喷嚏等……要知道,老太婆在这一整个圈套中饰演的但是雷同于“死尸”的角色,她的脸上绝对不能有丝毫抖动的陈迹,身体同样如此。试想一下,假如那天晚上,川原店里的那只黑猫无意中接近老太婆的身体,而使得老太婆的周身或是脸上有什么过激的反映,那老先生这么多天来辛苦安排的所有筹划都会被打乱,所以那晚猫的呈现才会让老先生十分紧张。 5、尾声 转眼一个多月的时间过去了,德云镇又恢复了往日的祥和与安宁,一切安静如初。 川原的剪发店一如既往营业,只是关门的时间提早了。关于这一点,他给别人的理由是不想工作太累,可其实只有他自己知道,那天晚上发生的事对他的影响真的很大。纵然他知道那一切是假的,可他仍然耿耿于怀,可是详细介意什么,他自己也说不上来。不过有一点他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他已经不再是名地隧道道的无神论者了。 夜幕尾随习习冷风而来,遮云蔽日,沉没了行人萧索的身影。路上黄叶飘落,凄清寂寥,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森森肃杀之气。 川原站在剪发镜前,心头突然罩上一层不安,他精神恍惚地看了眼屋外,登时怔住了,透过玻璃门屋外情形出现出的压抑,竟和那天晚上配偶俩呈现前的气氛千篇一律。川原感受自己的双腿有点儿发软了,街头的萧条让他感受十分不适应,仿佛一切又都回到了那天晚上。 风骤然刮得紧了,撞得店门哐哐作响,那种声音就似用铁锹不断拍打棺木时发出的声响,让川原感受很不惬意。老旧的店门禁不起疾风肆虐,不消一会儿就被撞开了。强劲的凉风霎时如万丈巨浪般袭来,吹得川原寒毛直竖,满身乱颤不止。 店里的吊灯开始摇晃,灯光忽明忽暗,俏皮地装点着川原慢慢变青的表情。街上的沙尘与废纸屑通通给这刹时加强的怪风卷了进来,来势之快竟叫人有点猝不及防,污物在屋里胡乱沾染,险些把周遭的一切从新“掩饰”了一遍。 川原虽对这突如其来的大风甚是希奇,可并没有多想,他一边用手护住自己的眼睛以免污物飞入,一边快步移至门面试图关紧店门。就在这时,一只惨白的手从漆黑中伸了进来,死死拽住川原的衣角——那是一只枯竭干瘦的手! 川原僵直地立在原地,一时之间竟不知作何反映,两只充血的眼睛惊惶地睁着,仿佛将近爆裂开来。 风突然间止了,吊灯停止了摆动,店里的照明恢复了原样,漆黑中的那只手逐渐清楚起来。借着灯光,川原终于看清了手的主人——那是一张上了年龄的女性的面孔,不再细嫩的脸上划满了深一道浅一道的皱纹,这些皱纹让原本立体的面部五官萎缩成一团,看上去更像一颗干瘪的梨。她歪扭着身体,瘫坐在一张锈迹斑斑的轮椅上,凹陷的脖子像是断了筋,无力地偏心一侧,致使齐肩短发极不自然地遮住了她的双眼。 也不知是从哪儿来的勇气,川原突然有种想一睹那女性眼睛的激动。因为人们常说,只要直视对方的眼睛,就可以知道那个人有没有在对你撒谎。也许川原就是想履行一下这套理论,显然他再也无法容忍别人继续用“装鬼”这类伎俩来嘲弄自己了。 川原战战兢兢地将手伸了出去,轻轻撩开笼罩在女性眼睛上的那缕头发。 四周静谧得很诡异,阴冷的月光柔柔地洒在川原惊骇的脸上。突然,川原一直抿着的嘴微微张开,露出一副让人胆寒的笑容,细声细语道:“本来你基本没有眼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