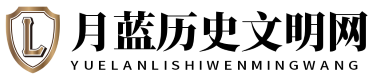钱理群今天我们为什么需要鲁迅
鲁迅研究界就或隐或显地存在着一种倾向:在将“鲁迅凡俗化”的旗号下,消解或削弱鲁迅的精神意义和价值。这又显然与消解理想,消解精神的世俗化的时代直接相关。

(作者:钱理群,北大中文系教授)
有一部电影叫《鲁迅》,我对这部电影的印象也很不错,能拍成这样,是很不容易了。在拍摄过程中,编剧和导演曾经征求过我的意见,因此我注意到编剧的一个陈述,强调鲁迅“兼有‘儿子’、‘丈夫’、‘父亲’、‘导师’、‘朋友’等几重身份”,整部电影也是围绕这五方面来展开的,着重从日常生活中来展现鲁迅情感的丰富,同学们看了电影以后,觉得亲切而感人,这说明电影是成功的,它有助于年轻一代走近鲁迅。但我可能受到鲁迅的影响,喜欢从另一面来看来想,于是,就有了这样的疑问:“今天我们花了这么大的人力、物力来拍这么一部大型彩色故事片,难道仅仅在于告诉今天的观众:鲁迅是一个好儿子,好丈夫,好父亲,好朋友吗?”这其实就内含我们今天所要讨论的问题:历史与现实生活中,我们中国并不缺少好儿子,好父亲,好丈夫,但我们为什么需要鲁迅呢?这正是我们所要问的:鲁迅对于,对于我们民族的特殊的,仅仅属于他的,非他莫有的,意义和价值在哪里?
提出这样的问题,并不是无的放矢:因为在当下的思想文化界,鲁迅研究界就或隐或显地存在着一种倾向:在将“鲁迅凡俗化”的旗号下,消解或削弱鲁迅的精神意义和价值。这又显然与消解理想,消解精神的世俗化的时代直接相关。
是的,鲁迅和我们一样:他不是神,是人,和我们一样的普通人。
但,鲁迅又和我们,和大多数中国人不一样:他是一个特别,因而稀有的人。因此,我们才需要他。
这样说,强调这一点,不是要重新把他奉为神,重新把他看作是“方向”,“主将”,“导师”。——这些说法,恰恰是掩盖了鲁迅真正特别之处。
鲁迅从来就不是任何一个现代思想文化运动的“主将”,无论是二十年代的五四新文化运动,还是三十年代的左翼文学、文化运动,他都是既支持,参加,又投以怀疑的眼光。
鲁迅从来就不是,也从来没有成为“方向”,他任何时候(过去,现在和将来)都不可能成为“方向”,因为他对任何构成“方向”的主流意识形态,以至“方向”本身,都持怀疑、批判的态度。
而且,鲁迅还向一切公理,公意,共见,定论——,提出质疑和挑战。——画家陈丹青按胡塞尔的定义:“一个好的怀疑主义者是个坏公民”,断定“不管哪个朝代”,鲁迅“恐怕都是坏公民”,这是确乎如此的:鲁迅就是一个“好的怀疑主义者”和“坏的公民”。
鲁迅也不是导师。从古代到现代,到当代,绝大多数的中国知识分子都有一个“导师”和“国师”情结,这可以说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个传统。鲁迅是提出质疑和挑战的少数人之一。他在著名的《导师》一文里说,知识分子自命导师,那是自欺欺人,他提醒年轻人不要上当;但他又说,我并非将知识分子“一切抹杀;和他们随便谈谈,是可以的”。在我看来,他也这样看自己:他不是“导师”,今天我们读者,特别是年轻读者如果想到鲁迅那里去请他指路,那就找错了人,鲁迅早就说过,他自己还在寻路,何敢给别人指路?我们应该到鲁迅那里去听他“随便谈谈”,他的特别的思想会给我们以启迪。是“思想的启迪”,和我们一起“寻路”;而非“行动的指导”,给我们“指路”:这才是鲁迅对我们的意义。
而鲁迅思想的特别,就决定了他对我们的启迪是别的知识分子所不能替代的,是他独有的。
鲁迅思想的特别在哪里?同学们从我刚才连说的三个“不是”——不是“主将”,不是“方向”,不是“导师”,就可以看出,鲁迅在整个思想文化体系、话语结构中,始终处于边缘地位,始终是少数和异数。
他和以充当“导师”、“国师”为追求的知识分子的根本区别,就在于他从不看重(甚至藐视)社会、、思想、文化、学术的中心位置,他也不接受体制的收编,他愿意“站在沙漠上,看看飞沙走石,乐则大笑,悲则大叫,愤则大骂”,他就是要在体制外的批判中寻求相对的思想的独立与自由。——当然,他更深知,完全脱离体制的控制是不可能的,独立和自由极其有限,他甚至说,这是“伪自由”:他连自己的追求也是怀疑的。
而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大讲“正统”、“道统”,同化力极强的文化结构与传统来说,这样的“好的怀疑主义者”,这样的体制外的,边缘的批判者,是十分难得而重要的;我们甚至可以说,中国现代思想文化,幸亏有了鲁迅,也许还有其他的另类,才形成某种张力,才留下了未被规范、收编的别一种发展可能性。
我们这里所说的“收编”,是一个广泛的概念,不只是指体制的收编,也指文化,例如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的收编。这就说到了鲁迅的另一个特别之处:他的思想与文学是无以归类的;鲁迅因此专门写了一篇文章:《谈蝙蝠》,文章特意提到一则寓言:“鸟兽各开大会,蝙蝠到兽类去,因为他有翅子,兽类不收,到鸟类去,又因为它是四足,鸟类不纳,弄得他毫无立场”:鲁迅显然将他自己看作是中国思想文化界的“蝙蝠”。这是很能显示鲁迅的本质的:他和自己所生活的时代,存在着既“在”又“不在”的关系;他和古今中外一切思想文化体系,也同样存在着既“是”又“不是”的关系。他真正深入到了人类文明与中华民族文明的根柢,因此,他既能最大限度地吸取,“拿来”,又时时投以怀疑的眼光,保持清醒,既“进得去”(而我们许多人都只得其表,不得入门),又“跳得出”(而我们一旦入门,就拜倒在地,被其收编),始终坚守了思想的独立自主性,主体性。他的既“在”又“不在”,既“是”又“不是”的“毫无立场”,正是从根本上跳出了“非此即彼,非黑即白”的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和“站队”意识,而对一切问题,都采取了更为复杂的分析态度,形成了他的思想和表达的缠绕性。这也就使他最易遭到误解与各方攻击,在现实生活中,他就不得不时时处在“横战”状态中。但这同时就使他的思想与文学具有了许多超越时代的未来因素,是同代人,甚至后几代人(他们常常拘于二元对立不能自拔)所不能理解,或只能片面理解,而要在历史的复杂性逐渐显露之后,才能为后来人所醒悟;或者说,当后来人面对更为复杂的现实时,鲁迅思想与文学的启示性才真正得以显示,并获得新的现实性:我们今天读鲁迅著作,总能感到他仍然生活在我们的现实中,其原因即在于此。
我们在这里已经讨论到了,鲁迅这样的中国现代思想文化中的少数,异数,这样的无以归类的“蝙蝠”,对今天的中国思想文化界,今天的中国读者的意义。
首先,它是一个检验:能否容忍鲁迅,是对当代,以及未来中国文化发展的宽容度、健康度的一个检验。而我们这里所发生的,却是人们争先恐后地以各种旗号(其中居然有“宽容”的旗号)给鲁迅横加各种罪名。尽管明知道这种不相容是鲁迅这样的另类的宿命,今天的新罪名不过是鲁迅早已预见的“老谱袭用”,但我仍然感到悲哀与忧虑,不是为鲁迅,而是为我们自己。
当然,任何时候,真正关注,以至接受鲁迅的,始终是少数:一个大家都接受的鲁迅,就不是鲁迅了。我曾在《与鲁迅相遇》里说过:“人在春风得意,自我感觉良好的时候,大概是很难接近鲁迅的,人倒霉了,陷入了生命的困境,充满了困惑,甚至感到绝望,这时就接近鲁迅了”。换一个角度说,当你对既成观念、思维,语言表达方式,深信不疑,或者成了习惯,即使读鲁迅作品,也会觉得别扭,本能地要批判他,拒绝他;但当你对自己听惯了的话,习惯了的常规,常态,定论,产生不满,有了怀疑,有了打破既定秩序,冲出几乎命定的环境,突破自己的内心欲求,那么,你对鲁迅那些特别的思想、表达,就会感到亲切,就能够从他那里得到启发。这就是鲁迅对我们的意义:他是另一种存在,另一种声音,另一种思维,因而也就是另一种可能性。
而鲁迅同时又质疑他自己,也就是说,他的怀疑精神最终是指向自身的,这是他思想的彻底之处,特别之处,是其他知识分子很难达到的一个境界。因此,他不要求我们处处认同他,他的思想也处在流动、开放的过程中,这样,他自己就成为一个最好的辩驳对象。也就是说,鲁迅著作是要一边读,一边辩驳的:既和自己原有的固定的思维、观念辩驳,也和鲁迅辩驳,辩驳的过程,就是思考逐渐深入的过程:在鲁迅面前,你必须思考,而且是独立地思考。正是鲁迅,能够促使我们独立思考,激发我们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他不接受任何收编,他也从不试图收编我们;相反,他期待,并帮助我们成长为一个有自由思想的,独立创造的人——这就是鲁迅对我们的主要意义。
而我还想强调一点:我们今天所面临的,是一个矛盾重重,问题重重,空前复杂的中国与世界。我自己就多次发出感慨:我们已经失去了认识和把握外在世界的能力,而当下中国思想文化界又依然坚持处处要求“站队”的传统,这就使我这样的知识分子陷入了难以言说的困境,同时也就产生了要从根本上跳出“二元对立”模式的内在要求。我以为,正是在这样的思想文化背景下,鲁迅的既“在”又“不在”,既“是”又“不是”的“毫无立场”的立场,对一切问题都采取更为复杂的缠绕的分析态度,就具有了一种特殊的意义。而鲁迅思想与文学的独立自主性,无以归类性,由此决定的他的思想与文学的超时代性,也就使得我们今天面对我们自己时代的问题,并试图寻求新的解决时,鲁迅的思想与文学或许是一个特别值得注意和重视的精神资源。
更难能可贵的是,鲁迅同时又是一个能够将自己的思想追求变为实践的知识分子。他的前述边缘的,异类的,反体制的思想立场,注定了他在现实社会结构中,必然站在社会底层的“被侮辱和被损害者”这一边,为他们“悲哀、叫喊和战斗”:这正是鲁迅文学的本质。同时,他又怀着“立人”的理想,对一切方面,一切形式的对人的个体精神自由的侵犯,对人的奴役,进行永不休止的批判,因此,他是永远不满足现状的,因而是“永远的批判者”:这也正是鲁迅思想的核心。鲁迅曾提出一个“真的知识阶级”的概念,其主要内涵就是以上所说的两个方面:永远站在底层平民这一边,是永远的批判者。这也是鲁迅的自我命名。这样的“真的知识阶级”的传统,在当下中国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这是我们今天需要鲁迅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
有人在贬低鲁迅的意义时,常常说鲁迅只有破坏,没有建设。他们根本不理解鲁迅思想本身,就是对中国思想文化的建设性贡献,是二十世纪中国和东方思想文化遗产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而就具体操作的层面,在我看来,也很少有人像鲁迅这样为中国的文化建设和积累而沤心沥血:这自然是否定者视而不见的。鲁迅早就说过:“我已经确切的相信:将来的光明,必将证明我们不但是文艺上的遗产的保存者,而且也是开拓者和建设者”。鲁迅是把这样的信念化作日常生活具体行为的。早在二十年代,他就提倡“泥土”精神,提出“不要怕做小事业”。直到1936年去世之前,他还呼吁“中国正需要做苦工的人”。他自己就是文化事业上的“苦工”,仅1936年生命最后一段历程,他就以重病之身,编校了自己的杂文集《花边文学》、小说集《故事新编》,翻译《死魂灵》第二部,编辑出版亡友瞿秋白的《海上述林》,编印《〈城与年〉插图本》、《〈死魂灵〉百图》、《珂勒惠支版画选集》,还参与编辑《海燕》、《译文》等杂志。他的生命就是耗尽在这些点点滴滴的,具体琐细的小事情上,但他生命的意义,也就体现在这些在鲁迅看来对中国,对未来有意义的小事情上。这倒是显示了鲁迅“平常“的一面:鲁迅经常把他的工作,比做是“农夫耕田,泥匠打墙”,这正是表明了鲁迅精神本性上的平民性。这是鲁迅的平凡之处,也是他的伟大之处。在我们今天这个浮躁、浮华的,空谈的时代,或许我们正需要鲁迅这样的文化“苦工”。
人学研究网·千秋人物栏目编辑:莫如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