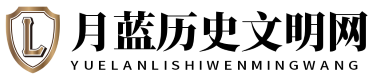阎克文我们的同时代人韦伯
韦伯从事这场旷日持久的斗争,并非挑起一场见仁见智的意识形态厮杀,而是无意中开创了现代社会科学的一个新,用他自己的话说,他是“以学术为业”。

(作者:阎克文,山东大学当代研究所教授,韦伯研究专家)
很大程度上甚至可以说,马克斯·韦伯几乎是在与“马克思主义”的斗争中度过了一生的。当然,韦伯从事这场旷日持久的斗争,并非挑起一场见仁见智的意识形态厮杀,而是无意中开创了现代社会科学的一个新,用他自己的话说,他是“以学术为业”,尽管他的思想影响所及并不止于学术领域。
作为世界性的学术共识,《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下称《新教伦理》)被看做这个新的开端,应该是恰如其分的。它剖析了一个巨大的历史切片,用帕森斯的评价来说,“是韦伯首先将价值观在决定人的社会行动时的作用问题提到了理论高度”。结果是,它从根本上遏阻了“经济决定论”的无限制泛滥,即便说它力挽狂澜,无疑也不能算是夸大其词。这个命题的出现已近百年,今天仍在强烈刺激着中国的现代性问题意识,表明它的解释力依然生动如初。当然,一直都有论者认为,它作为一个需要实证主义证据支持的命题,也并不是无懈可击,更不能包打天下,否则就很难甚至无法解释越来越多非西方地区的现代性转型历程。关于这样的质疑,今天也许可以言之凿凿地说,基本上是对文本的片面理解所致,因为韦伯本人在文本的最后已有明确表示,这只是为一项大规模研究预作准备,而不是提前为那项研究做出的结论。因此,对于有兴趣的中文读者来说,准确理解这个文本就不难看出,一个逻辑链条的开放性并不是它的漏洞,毋宁说是为它预留了更大的扩展空间。
我们从《新教伦理》的论述中,已经可以生动地感受到观念对于历史过程的独特魅力和推动作用。随后的几部系列研究,即《儒教与道教》《印度教与佛教》《古代犹太教》(非常可惜的是,韦伯未及完成规划中的伊斯兰教研究),构成了韦伯名之为“世界诸宗教的经济伦理”(以下简称“经济伦理”)的专题论丛,把这种作用的多样性展示得更为饱满。然而,《新教伦理》的广泛影响,本已使韦伯受到了德国学界很长时间的误解,“经济伦理”似乎又加深了这样的误解,简言之,他甚至被看做一个文化决定论者。对此,韦伯生前就做过多次回应,希望澄清人们的误读和偏见。随着他的著作文本越来越多地在欧美地区被译介、传播和研究,局面早已发生了根本改观。无独有偶,1980年代韦伯在中国声望日隆,也是从《新教伦理》的译介开始的,所以毋庸讳言,中文读者对韦伯的认识也曾普遍误入同样的歧途,以致今天是否对韦伯的“文化类型学”已经有了一个比较普遍的共识,恐怕还很难说,这里的重要原因之一,同样是对文本了解不足。然而,至少从目前我们能够得到的韦伯著作中译本来说,继续重复过去对韦伯的那种误解,显然已经没有太多的客观理由了。
一些与现代世界的由来及其可能的发展方向有关的大问题,可以说是吸引韦伯思考了一生的问题。他试图为这些问题找到理论上更经得起挑剔、重要的是经验上更有说服力的答案。如果说“经济伦理”只是给出了普遍历史(universalhistory)的若干剖面的话,那么《经济与社会》则是构建了一个庞大的类型学脚手架,以期整合极为多样化的要素,从中寻求对历史现实的因果说明。尽管这个脚手架的结构纵横交错,十分复杂,但它被广泛接受的程度,早已表明了它的学术与思想地位,教科文组织1949年发起在奥斯陆成立的国际社会学协会(ISA),1998年将此书评为20世纪最重要的社会学著作,其价值当毋庸置疑。但另一方面,就我们这里的情况而言,无论是整个社会科学领域还是在次级学科领域,总体上来看,它的影响恐怕只能说还处在一个相当初级的状态,也就是单向的文本接受阶段,真正完整、深入的解读与研究者,殊可谓严格意义上的屈指可数,不论这是什么原因所致,与它在欧美备受推崇并且激发了经久不衰的批判性评价和学术论战相比,与我们这里日趋张大的人文学科建设规模以及对思想学术资源持续加深的普遍需求相比,毕竟算是个非常尴尬的局面。
著名韦伯研究专家、韦伯原著的权威英译者京特?罗特(GuentherRoth)认为,“《经济与社会》第一次从世界历史的深度对社会结构与规范性秩序进行了经验比较。如此来说,它超越了始终在冥思苦想要建立某种社会科学的大量‘体系’。”不难看到,《经济与社会》也已经为我们对自身历史现实的关切注入了富有活力的代谢因子。如果说,最初对《新教伦理》的热情误读,在某种程度上是对粗鄙化的“唯物主义”意识形态体系的逆反表现,难免带有矫枉过正的普遍特征,但随后却刺激了对中国现代性转型过程中本土文化资源问题的广泛思考与争论,而且至今势头不减,也不失为修成正果,那么,《经济与社会》从一开始就是以润物细无声的姿态进入公共话语的。《新教伦理》本来就是一场思想学术论辩的产物,而且是韦伯学术著作中语言最为平易、最为奔放的作品,立竿见影的感召力之强大实不足为怪。《经济与社会》则大为不同,它是一整套尽最大可能保持了“价值中立”的认识论分析手段,就其技术意义而言,用京特?罗特的话说,“它是要为经验研究奠定一个各执己见的人们都能接受的共同基础”,而事实上,这也正是《经济与社会》历久弥新的深厚奥秘所在。因此,韦伯开创的一系列概念范畴和观念解析方法,以及由此形成的逻辑架构,就不可能以价值宣言式的轰动效应见长,而是迫使读者不得不以知识的诚实和思想训练的素养审视它们给出的画面并作出反应。至少从现象上看,韦伯关于社会行动、正当性秩序、官僚制(科层制)、超凡魅力、宗教信仰与经济行为等多方面的系统论述,以及他着力阐发的理性化理论,都已在不知不觉中逐渐融入了众多学科乃至某些非学术领域的日常话语,足以见出这部百科全书的思想渗透力。考虑到这不过是最近十年间的变化,而且是学术环境大踏步行政化兼商业化的十年,还能有这样的播变,也确实殊为不易了。
韦伯曾打算用一篇提纲挈领的文字介绍一下当时尚未成书的《经济与社会》概貌,但最终还是放弃了这个打算。由此也不难推知,对这样的巨著进行扼要概括,也许连作者本人都没有把握能否避免简单化甚至教条化的危险。但尽管如此,《经济与社会》谋篇立意的基本脉络还是清晰可见的,而且从一开篇就是如此:“解释性理解社会行动并对其进程与结果进行因果说明”。这里说的“行动”,“指的是行动中的个人给他的表现附着了某种主观意义”,“社会行动则是指该行动的主观意义还顾及到了他人的表现,并据此作为行动进程的取向”。这个严谨的表述在今天看来好像已经没有什么不同寻常之处,但若考虑到黑格尔“时代精神”(Zeitgeist)观念和庸俗唯物论对那个时代潮流的强大影响,也许就不难看出,它这是不动声色地指出了一个普适性的经验事实,即个人并不是什么社会关系的总和,而是社会关系的基本单元,社会关系是从个人开始,而不是相反,从而在根本上划清了与有机论、原子论、机械论、进化论直至各种单一因果决定论的界限,不言而喻,这个一般性的哲学前提,对于后面有关正当性秩序及其理性化的比较研究和系统论述,意义非同小可。不过,就笔者陋见所及,这样的价值背景目前尚未进入学界的主流视线,因而不少论者难免囿于对韦伯各个类型学范畴的孤立审视和简单套用。
对于置身一种特殊意识形态语境的中文读者来说,《经济与社会》最具冲击性的力量大概在于,它彻底颠覆了一个流行至今但十分粗糙的历史观,亦即历史上的所有经济结构,乃是所有既定历史现实的主要的、甚至唯一的决定性因素。甚至可以这样认为,往最简明扼要处说,《经济与社会》洋洋百余万言,首先就是用“决定性因素之一”否定了“唯一的决定性因素”。其次但更为重要的是,它无可争辩地厘清了在社会关系中发育、生成和衍变的社会行动秩序背后,存在着若干相对独立但彼此作用的力量。因为,《经济与社会》作为一个脚手架,在对特定历史现象的说明方面,让我们看到的是跨时代、跨文化的类型建构,在对特定历史事件的分析方面,让我们看到的是多元要素的互为因果。从韦伯的著述来看,也正是基于对这些力量和要素的准确把握,才使韦伯不幸成了一位现代耶利米,因为他准确预见到了在他生前身后德国将要一再遭受的历史命运,以及日趋理性化的现代世界的不确定性。相形之下,那种理论上超历史的“历史规律”,却是和历史本身格格不入的。
韦伯的著述体系之广博与复杂程度,恐怕很难以简明扼要的方式再现出来。但从思想资源的价值上说,我们自身的现代性关切如果还能避免误入绝对主义的死胡同,或者相反,避免陷入相对主义的烂泥潭,韦伯无疑还会长期给我们提供独到的意义,很多学者都认为,其中尤为核心的是他的方体系。一百多年后的今天也许可以看得更清楚,如果没有这个既复杂又精致的方体系,恐怕很难想象韦伯的整个著述成就还能有如此历久常新的资源性价值。上个世纪的最初十年间,韦伯先后写出五篇论文和一部论著,作为韦伯的元理论著作,相当完整地阐明了他的社会科学方立场。其中的两篇论文和后来为1913年社会政策协会会议准备的备忘录曾被结集译成英文(此书已有中译本,即《社会科学方》,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另外三篇论文目前尚未见有中译);那部论著RoscherundKniesunddielogischenProblemederhistorischenNationalokonomie,始作于韦伯大病未愈的1902年,完成于1905年(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出版了中译本,书名为《罗雪尔与克尼斯:历史经济学的逻辑问题》)。这些总共五百页左右的文论,无疑可以看作韦伯著述体系之堂奥,举凡韦伯思想中的内在张力和他的比较研究方略,都可以追溯到此,其中,关于理性行动的理想类型和社会科学领域的价值中立问题,韦伯的原创性论述产生了尤为深入的思想学术影响。
韦伯提出的多论域问题和命题,至今还是我们绕不过去的审视对象,就此而论,正如《韦伯学术思想评传》的作者所说,生于一个半世纪之前的韦伯,至今还是“我们的同时代人”。这当然不是说我们可以从他那里找到解决我们自身问题的现成答案,而是他的启示价值仍然难以忽视,尽管理解这一点对于中文读者来说绝非一蹴而就之功。
韦伯如今已经成为德国的一个文化象征,小学课程中就有专门讲授韦伯生平故事的安排,中学到大学的系统讲授更可想而知。他25岁时的博士论文,至今还是众多欧美大学相关专业学生的必读参考书。世界各地对韦伯的研究文献,更可谓汗牛充栋,不可胜数。在这方面,中国的现状确实大不如人意。不过还有另一方面。韦伯的著述规模相当惊人,到目前为止,德国人根据韦伯遗稿编辑成书的德文新版韦伯全集已有46卷,包括著作与演讲、讲义与笔记、书简三个部分,其中已正式出版的共35卷。陆续译成英文的单行版本目前有17种,这些英译本迄今已全部有了中译本,大约为新编德文版全集的15卷规模,虽然离再现韦伯思想的全貌还有很大差距,但基本上涵盖了韦伯著作的主体部分。仅就文本翻译而言,中译的进展并不逊于英语世界,而且,尽管韦伯的著作不可能是畅销书,但出版界的热情始终不减,比如二十多年来,《新教伦理》已有11个出版社印行了13个翻译版本,甚至《经济与社会》也能一再重印,这同时也说明了中文读者的需求具有长期的刚性潜力,无疑是在一个貌似异质的文化语境中体现了韦伯的世界性思想学术地位和资源性价值。虽然十分遗憾的是,官方对此迄今无积极态度和任何实际的支持,但终于,在学界的自发努力下,已经有了从德文版翻译韦伯全集的规划,最近还在山东大学设立了“韦伯研究中心”,负责协调组织落实,倘假以时日,当能不负众望,为今后的韦伯研究提供更加接近原著的文本基础。
人学研究网·千秋人物栏目责编:莫如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