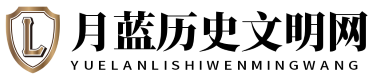钱穆道家思想
先秦道家,主要惟庄老两家。此两人,可谓是中国道家思想之鼻祖,亦为中国道家思想所宗主。后起道家著述,其思想体系,再不能越出庄老两书之范围,亦不能超过庄老两书之境界。 (一) 中国思想,常见为浑沦一体。极少割裂斩截,专向某一方面作钻研。因此,其所长常在整体之融通,其所短常在部门之分析。故就中国思想史言,亦甚少有所谓思想之专家。今欲讨论道家思想,则亦惟有从道家思想之全体系中探究而阐述之。又所谓儒墨道法诸家之分派,严格言之,此亦惟在先秦,略可有之耳。至于秦汉以下,此诸家思想,亦复相互融通,又成为浑沦之一新体,不再有严格之家派可分。因此,研治中国思想史,分期论述,较之分家分派,当更为适合也。故此篇所论道家思想,亦仅以先秦为限断。 先秦道家,主要惟庄老两家。此两人,可谓是中国道家思想之鼻祖,亦为中国道家思想所宗主。后起道家著述,其思想体系,再不能越出庄老两书之范围,亦不能超过庄老两书之境界。然此两书,其著作年代先后,实有问题。据笔者意见,《庄子》内篇成书,实应在《老子》五千言之前。至《庄子》外杂篇,则大体较《老子》为晚出。庄子生卒年世,当与孟子略同时,而《老子》成书,则仅当稍前于荀子与韩非。惟此等考订,则并不涉本篇范围。而本篇此下之所论述,实亦可为余所主张庄先老后作一旁证也。 (二) 先秦思想,当以儒墨两家较为早起,故此两家思想,大体有一共同相似之点,即其思想范围,均尚偏注于人生界,而殊少探讨涉及宇宙界是也。故孔子言天命,墨子言天志,亦皆就人生界推演说之。此两人之立论要旨,可谓是重人而不重天。庄子晚出,承接此两人之后,其思想范围,乃始转移重点,以宇宙界为主。《庄子》书中论人生,乃全从其宇宙论引演。故儒墨两家,皆本于人事以言天,而庄周则本于天道而言人,此乃其思想态度上一大分别也。 然若更深一层言之,在庄周意中,实亦并无高出于人生界以上之所谓天之一境。庄周特推扩人生而漫及于宇宙万物,再统括此宇宙万物,认为是浑通一体,而合言之曰天。故就庄子思想言之,人亦在天之中,而同时天亦在人之中。以之较儒墨两家,若庄周始是把人的地位降低了,因其开始把人的地位与其他万物拉平在一线上,作同等之观察与衡量也。然若从另一角度言,亦可谓至庄周而始把人的地位更提高了,因照庄周意,天即在人生界之中,更不在人生界之上也。故就庄周思想体系言,固不见有人与物之高下判别,乃亦无天与人之高下划分。此因在庄周思想中,天不仅即在人生界中见,抑且普遍在宇宙一切物上见。在宇宙一切物上,平铺散漫地皆见天,而更无越出于此宇宙一切物以上之天之存在,此庄周思想之主要贡献也。 就于上所分别,乃知庄周与儒墨两家,在道字的观念上,亦显见有不同。儒墨两家,似乎都于人道之上又别认有天道。而庄周之于道,则更扩大言之,认为宇宙一切物皆有道,人生界则仅是宇宙一切物中之一界,故人生界同亦有道,而必综合此人生界之道,与夫其他宇宙一切物之道,乃始见庄周思想中之所谓之天道焉。故儒墨两家之所谓天道,若较庄周为高出,而庄周之所谓天道,虽若较儒墨两家为降低,实亦较儒墨两家为扩大也。 今若谓道者乃一切之标准,则庄周思想之于儒墨两家,实乃以一种解放的姿态而出现。因庄周把道的标准从人生立场中解放,而普遍归之于宇宙一切物,如是则人生界不能脱离宇宙一切物而单独建立一标准。换言之,即所谓道者,乃并不专属于人生界。骤视之,若庄周把儒墨两家所悬人生标准推翻蔑弃,而变成为无标准。深求之,实是庄周把儒墨两家所悬人生标准推广扩大,而使其遍及于宇宙之一切物。循此推演,宇宙一切物,皆可各自有其一标推,而人生亦在宇宙一切物之内,则人生界仍可有其人生应有之标准也。故庄周论人生,决不谓人生不能有标准,彼乃把人生标准下侪于宇宙一切物之各项标准而平等同视之。治庄周思想者,必明乎此,乃始可以把握庄周之所谓天,与其所谓道之真际也。 (三) 则仅是人生界中之一业,一现象,故论庄周之思想,亦当如我上举,就其言天言道之改从低标准与大标准处着眼,乃始可以了解庄周论之精义。此下试举较浅显者数例作证明。庄周云: 民湿寝则腰疾偏死,鳅然乎哉?木处则惴栗恂惧,猿猴然乎哉?三者孰知正处?民食刍豢,麋鹿食荐,鸱鸦嗜鼠,蝍且甘带,四者孰知正味? 此所举寝处与饮食,如就人生标准言,自当为宫室与豢刍。但庄周则偏不认此等标准为寝处饮食惟一的标准。庄周则偏把人与泥鳅猿猴麋鹿鸱鸦蝍且,拉平在一条线上,同等类视,合一比论,遂乃有三者孰知正处,四者孰知正味之疑问。然庄周之意,亦仅谓人生标准并非宇宙一切物之惟一标准而已。在庄周固非蓄意要推翻宇宙一切物之寝处与饮食之各有其标准也。宇宙一切物,既可各自有其寝处与饮食之标准,则人生界之自可有其人生之独特的寝处饮食之标准,亦断可知。故在庄周意,只求把此寝处饮食之标准放大普遍,平等散及于一切物,使之各得一标准。至于宫室之居,固为人生界之正处,而阴湿的泥洼,乃及树巅木杪,也同成为另一种正处。刍豢稻粱,固可为人生界之正味,而青草小蛇与腐鼠,亦同样可成为又一种正味。在庄周,只是把寝处与饮食的标准放宽了,而并非取消了。此一层,则每易为治庄周思想者所误解。其实庄周言道,只是放宽一切标准而平等扩大之,固非轻视一切标准而通体抹摋之也。 东郭于问于庄子曰:所谓道,恶乎在?庄子曰,无所不在。东郭子曰:期而后可。庄子曰:在蝼蚁。曰:何其下邪?曰:在稊稗。曰:何其愈下邪?曰在瓦甓。曰:何其愈甚邪?曰:在屎溺。 若依儒墨两家所揭举之标准言,则所谓道者,不上属天,即下属人。而庄周思想则不然。庄周谓宇宙一切物处皆有道,故宇宙一切物,皆可各有其自身之标准。因此生物之微如蝼蚁,如稊稗,甚至无生之物如瓦甓,乃至如屎溺,皆有道,即皆有其本身所自有之标准也。因此,宇宙一切物,莫非天之所于见,即莫非道之所于在。庄周乃如此般把道字的观念放宽了,同时亦即把道的标准放低了。但又当知者,既是蝼蚁稊稗瓦甓屎溺皆有道,岂有高至于人生界而转反没有道。故庄周之论道,骤视之,若见为无标准,深察之,则并非无标准。骤视之,若庄周乃一切以天为标准,深察之,则在庄周理论中,宇宙一切物,皆各有标准,而转惟所谓天者,则独成为无标准。若使天而自有一标准,则宇宙一切物,不该再各自有标准。若使宇宙一切物而各自没有一标准,则试问所谓天之标准者,又是何物乎?如此推寻,则仍必落入儒墨两家窠臼,即就此人生标准而推测尊奉之,使其为宇宙一切物之标准焉。而庄周思想则实不然。在庄周思想体系中,实惟天独为无标准,而即以宇宙一切物之种种标准而混通合一,即视之为天之标准也。换言之,在庄周思想体系中,乃平等地肯定了宇宙一切物,却独独没有于此宇宙一切物之外之上,另还肯定了一个天。庄周书中之所谓天,其实乃通指此宇宙一切物而言。于是此宇宙,在庄周思想中,乃有群龙无首之象。此即谓在于此一切物之外,更无一个高高在上之天,以主宰统领此一切物。于是宇宙一切物,遂各得解放,各有自由,各自平等。故此宇宙一切物,乃各有其本身自有之标准,即各自有一道。人生则下侪于宇宙一切物,人生亦自有人生所应有之标准,人生亦有道。但此人生界之标准与道,亦仅是宇宙一切物之各自具有其标准与道之中之一种。固不能如儒墨般,单独由人生上通于天,认为惟此人生界中之道与标准,独成其为天道与天则也。 (四) 此一思想体系,骤视之若放荡纵肆,汗漫无崖岸,其实亦自有其平实处。由于此种想法而落实到问题,则其见解亦自然会与儒墨有不同。此下再就此阐述。 在庄周思想中,既不承认有一首出庶物之天,因亦不承认有一首出群伦之皇帝。既不承认有一本于此而可推之彼之标准与道,在一切物皆然,则人生界自亦不能例外。如是则在庄周思想中,乃不见人生界有兴教化与立法度之必要。因所谓教化与法度者,此皆悬举一标准,奉之以推概一切,求能领导一切以群向此标准,又求能限制一切使勿远离此标准。之大作用,主要亦不越此两项。于是在庄周思想中,事业遂若成为多余之一事。 肩吾见狂接舆,狂接舆曰:日中始何以语女?肩吾曰:告我君人者,以已出经式义度,人孰敢不听而化诸?接舆曰:是欺德也。……鸟高飞以避缯弋之害,鼷鼠深穴乎神丘之下,以避薰凿之患,而曾二虫之无知! 夫鸟能高飞,鼠能深穴,彼既各有其天,斯即各有其道。鸟鼠尚然,何况人类。今不闻于鸟鼠群中,必须有一首出侪偶者君临之,以自出其经式仪度来教导管制其他之鸟鼠。则人类群中,又何必定需一政府,一君人者之教导与管制? 循此推论,庄周应是一无政府主义者,但庄周书中,则并未明白严格说到此一层。庄周只谓,一个理想的君,必能 游心于淡,合气于漠,顺物自然,而无容私焉,而天下治。 庄周并未明白主张无君沦,庄周亦未明白主张不要一切与政府。彼只谓一个理想之君,须能存心淡漠,顺物之自然,而不容私。庄周之所谓私,即指君人者私人之意见和主张。由于此等私人之意见和主张,而遂有所谓经式义度。如是则有君即等于无君,有政府亦将等如无政府。远自儒墨兴起之前,皇帝称为天子,即以上拟于天,庄周似乎并未完全摆脱此种思想传统之束缚。然就庄子思想言,天既是一虚无体,则皇帝亦该成为一虚无体,在此虚无体上却可发生理想许多的作用。 阳子居问老聃以明王之治,老聃曰: 明王之治,功盖天下,而似不自己。化贷万物,而民勿恃。有莫举名,使物自喜。立乎不测,而游乎无有者也。 此乃庄周所想像,以一虚无之君体,而可发生绝大的作用也。此一说,殆为此下《老子》五千言所本。故老子曰: 大道汜兮其可左右。万物恃之而生而不辞,功成不名有,衣食万物而不为主。 此章所言为大道。老子又曰: 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是谓元德。 所章所言是元德。其实此两章所言者皆是天。庄子理想中之理想,所谓明王之治者,即为其能与天同道,与天合德。一切物皆各原于天,但天不自居功,故万物皆曰我自然。惟其皆曰我自然,故各自恃而勿恃天。虽有天之道,而莫举天之名,故使万物皆自喜。明王之治,亦正要使民自恃,使民自喜,而皆曰我自然。如此,则在其心中,更不知有一君临我者之存在。此君临人群之明王,则俨然如天之临,虽有若无,成为一虚体。虚体不为一切物所测,亦不为一切物所知。此乃庄周理想人群之大自在与大自由,亦可谓是庄周思想中一番主要之大理论,亦竟可谓之是一番无君无政府之理论也。 故庄周又云: 南海之帝为儵,北海之帝为忽,中央之帝为浑沌。儵与忽时相与遇于浑沌之地,浑沌待之甚善。儵与忽谋报浑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窍,以视听食息,此独无有。尝试凿之。日凿一窍,七日而浑沌死。 一切物皆有知,皆有为,皆自恃,皆自喜,天独无知,又无为,因此天独不见有所恃,有所喜。一切有知有为之物,则莫不各有其自有之标准与道,因此一切物皆平等、皆自由。惟天高出一切物之上,故天转不能私有一标准与私有一道。若天亦自有一标准与道,则一切物既尽在天之下,一切物岂不将尽丧其各自之标准与道,而陷入于不自由,并其与天之标准与道将有合有不合,而陷于不平等。今使人生界中有一首出群伦之皇帝,此皇帝之地位既俨如自然界中之有天,故此皇帝,就理想言,亦必无知与无为,无所恃又无所喜,等于如没有。故一切人皆可各自有其一己所宜之标准与道,而君临其上之皇帝,则不能私有一标准,私有一道,甚至不该有七窍。因有了七窍,便自然会有知有为,因此遂自恃自喜,因此将自具标准,自有道,而如是便不应为帝王。 此乃庄周论政之大义。 上一页 1 2 3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