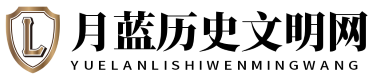东汉王朝与世界诸国的外交关系
东汉初期,匈奴虽不断南侵,汉、匈关系处在对立状态,但汉、匈两族人民之间,在当时战争较少的河西走廊一带,尚能维持较为密切的经济交换关系。

与匈奴的交往
东汉初期,匈奴虽不断南侵,汉、匈关系处在对立状态,但汉、匈两族人民之间,在当时战争较少的河西走廊一带,尚能维持较为密切的经济交换关系。《后汉书·孔奋传》载:建武时,“天下扰乱,唯河西独安,而姑臧(今甘肃武威县)称为富邑,通货羌(西羌)、胡(匈奴与杂胡),日市四合(每日交易四次)。每居县者,不盈数月,辄致丰积。”按古时市集交易,通例一日三合,今一日四合,足见此地人货殷繁。姑臧是汉、羌、匈奴、杂胡各族杂居错处的地方,从东汉初年此地合市一日四次看,当时北方各族人民间的经济联系是相当密切的。
南匈奴和东汉的关系十分友好。南单于“岁尽辄奉奏,送侍子入朝”,贡献礼物及汇报情况。“汉遣谒者送前侍子还单于庭,交会道路。”贺正月,拜陵庙,汉照例派谒者护送单于使,并赠送大批缯綵、锦、食物,甚至南方珍果“橙、桔、龙眼、荔支”等物给单于及其家属、左右贤王以下至骨都侯有“功善”者,即有功劳和表现好的人员,“岁以为常”。另外,每一单于死亡,汉朝都派使者前往,“吊祭慰赐”,又骨都侯已下”,并把这种做法列为常规。南匈奴内附,边境安宁,原来内徙的边郡居民,多陆续回归本郡,南匈奴人口增殖,社会生产逐渐恢复。东汉初期,为躲避匈奴奴隶主侵扰,北方边郡人民纷纷内徙,边地空荒。南匈奴内附之后,边境安宁,北地、朔方、五原、云中、定襄、雁门、代、上谷八郡,即今之甘肃庆阳、内蒙古河套、沿长城以北及晋北、冀北一带,人民陆续各还本土。南匈奴的人口,连同北匈奴陆续归附的及从战争俘虏的人口合计,到公元九十年前后,已有户三万四千、口二十三万七千多,胜兵五万多人,较之内附时的四、五万人,竟增加四、五倍之多。沿边诸郡的社会生产逐渐恢复。史称:“时南单于及乌桓来降,边境无事,百姓新去兵革,岁仍有年,家给人足。”由于南匈奴人入居塞内,分布沿边各郡,与汉人杂居,因而逐步转向定居和农耕生活,并且逐渐向东、向南迁徙。
与东亚国家的交往
西汉初年,诸部已与我国东北地区发生了经济交换关系。《史记·货殖列传》称燕“有鱼盐枣栗之饶。北邻乌桓、夫馀,东绾秽貉、、真番之利。”秦汉之际,我国北方人民因避乱迁往的不少。史称:“燕、齐、赵人往避地者数万口。”这些迁往的华夏之民,给当地经济、文化以积极的影响。如“辰韩,耆老自言秦之亡人,避苦役,适韩国,马韩割东界地与之。”其言语称谓“有似秦语,故或名之为秦韩”。由于其经济水平较高,故在当地“嫁娶以礼”,并用当地产的铁与其他部落进行交易,引进中原的先进文化,推动了经济、文化的发展。
东汉时,日本与汉有了进一步的联系。“建武中元二年(公元57 年),倭奴国奉贡朝贺,⋯⋯光武赐以印绶”。公元1784 年在日本福冈市志贺岛发现的“汉委奴国王”金印证实了此事。一般认为,“委(倭)奴国”在北九州的博多附近。这说明公元一世纪中期,日本北九州一带已与汉交通。安帝永初元年(公元107 年)冬十月,倭国遣使奉献。通过不断交往,中国的铁器、铜器、丝帛传往日本,丰富了倭人的物质文化生活。
与中亚、西亚、南亚地区诸国的经济、文化交流
通过“丝绸之路”,我国与中亚、西亚、南亚诸国进行了频繁的经济、文化交流。中国的铁器、丝绸和养蚕、缫丝技术,以及铸铁术、穿井法、造纸术都先后西传。
东汉章和元年(公元87年)及永元十三年(公元101 年),安息国两次把狮子和条支大鸟(又名安息雀,即鸵鸟)赠献给东汉朝廷。东汉明帝时印度佛教也传入中国。史称:明帝“遣使天竺问佛道法,遂于中国图画形象焉。楚王英始信其术,中国因此颇有信其道者。
与东南亚及西方诸国的友好往来
南海是泛指东南亚及印度洋地区等国而言。当时的番禺(今广州)、徐闻、合浦都是中国海外交通的重要口岸。
东汉初期,中国的一些农具制造技术和牛耕传到越南。如任延为九真郡太守,“乃令铸作田器,教之垦辟,田畴岁岁开广,百姓充给”。越南人民也倾慕中国,元和元年(公元84 年)春,“日南徼外蛮夷献生犀、白雉。”同年,究不事(今柬埔寨境内)邑豪到中国,赠送生犀、白雉。顺帝永建六年(公元131 年),叶调(今印度尼西亚境内)王便遣使者到东汉赠礼,帝赐金印紫绶。现古表明,印度尼西亚境内有许多汉代文物发现,可见当时两国间已有经济、文化往来。东汉时,与地处缅甸东部一带的掸国交往更为密切。永元九年(公元97 年),“永昌徼外蛮夷及掸国重译奉贡。”永宁元年(公元120 年)十二月,“永昌徼外掸国遣使贡献。”永建六年(公元131 年),“掸国遣使贡献。”
汉代,我国南海航路一般达到东南亚与印度洋地区,与欧洲的经济联系尚需安息、天竺等国中转。甘英由陆路想通使大秦,达波斯湾即被劝阻返回。但中国与欧洲的经济联系并未阻断,安息与天竺在其中起到中转作用。大秦“与安息、天竺交市于海中,利有十倍。”其王“常欲通使于中国,而安息图其利,不能得过。”大秦最需要的中国丝织品靠安息等国的间接贸易。大秦“又常利得中国丝,解以为胡绫,故数与安息诸国交市于海中。”《后汉书·西域传》一再提到:“(天竺)西与大秦通,有大秦珍物。⋯⋯和帝时,数遣使贡献。⋯⋯桓帝延熹二年、四年,频从日南徼外来献。”由此可知安息与天竺实为古代中国与欧洲罗马帝国海上贸易的重要枢纽。
随着中西贸易的发展,东汉时又开辟了自永昌入印度的一条航线。由于东汉势力在我国西南地区伸张的关系,滇缅通印度一路,得以畅达。《魏略·西域传》说:“大秦道既从海北陆通,又循海而南,与交趾七郡外夷比,又有水道通益州永昌,故永昌出异物。”所谓大秦有水道益州永昌,实自印缅中转,由孟加拉湾经缅甸进入中国西南地区,这较之绕道南洋更为便捷了。所以《后汉书》中所记“永昌徼外”蛮夷及掸国遣使译向汉贡献的记载次数最多。永宁元年(公元120 年),掸国王雍由调复遣使者到洛阳朝贺,“献乐及幻人能变化吐火,自支解,易牛马头。又善跳丸,数乃至千。自言我海西人,海西即大秦也。掸国西南大秦。”这次奉贡很可能又是通过永昌这条路线。可知,永昌(治今云南保山东北)成为我国和掸国,并与天竺、大秦等国进行通商贸易的又一集散地。
东汉中叶以后,从地中海越印度洋到南海的海路交通终于沟通。中国和罗马第一次发生了直接的外交联系。“延熹九年(公元168 年),大秦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徼外献象牙、犀角、玳瑁,始乃一通焉。”大秦王安敦即罗马皇帝马克·奥勒略·安敦尼阿斯(公元161—180 年在位)。这条记载又称: “其所表贡,并无珍异,疑传者过焉。”对这位使节是否真为罗马皇帝所派遣表示怀疑,因而引起中外史家的注意,千多年来,聚讼纷纭。但无可否认的是,即使是罗马商人假借罗马皇帝的名义和中国政府联系,企图得到一些商业上的优待。这也是东西方两大文明古国人民间第一次有记载的正式联系,其历史意义也是巨大深远而不容否定的。
参考文献:白寿彝:《中国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人学研究网人类文明通识智库·中华文明栏目责编:紫天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