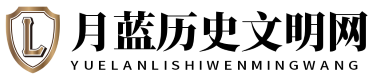郭齐勇现代三圣梁漱溟熊十力与马一浮
现代新儒学,大体上有三代学人。第一代学人中有梁漱溟、熊十力、马一浮等先生,三先生及其交往甚密,属于一个“文化共同体”。
现代新儒学,大体上有三代学人。第一代学人中有梁漱溟、熊十力、马一浮等先生,三先生及其交往甚密,属于一个“文化共同体”。我先分别介绍三先生的学术与人生,再讲他们之间的联系,他们的人格境界。
三先生的行迹

梁漱溟
梁漱溟先生(1893年-1988年)是一位性格特异、风骨嶙峋的人物。他是桂林人,但生长在北京。他并未接受过旧式教育,他的父亲很开明,让他在新式学堂里接受了小学、中学教育。1916年,24岁的梁先生在《东方杂志》上发表学习佛学的心得《究元决疑论》,得到北大蔡元培校长的赏识,蔡校长即与文科学长陈独秀商量,决定聘梁先生为特约讲师,讲授印度哲学。梁先生是20世纪面对西化狂潮最早肯定中国文化价值的文化人。其实他是非常主张科学与的,而且积极参与了建国的活动。
梁先生是有操守有气节的人,他的骨头很硬,我深深敬服他的人格。我曾经五次到北京看望、拜访他,为他的精神所折服。他是一位真儒,决不趋炎附势。他有自信力。1941年他在香港主持民盟事务,创办《光明报》。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陷,他坐小船回来,非常危险,但他若无其事,心地坦然地说:“我相信我的安危自有天命”。“我不能死,我若死,天地将为之变色,历史将为之改辙。”他说,孔孟之学的意蕴,中国文化在人类的地位,只有我能阐发,我还有三本书要写,我怎么能死呢?天怎么会让我死呢?梁先生就是这样自信,这样有担当意识的人。这很像孔子。如孔子所说的“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那样。解放前夕,他代表团体到昆明调查闻一多、李公朴遇害案,在群众大会上痛斥特务。他说,知识分子是杀不绝的,你们有胆量就朝我开枪,我不怕死。
抗战时与抗战后,他曾经两度去延安,曾经与多次交谈,乃至在窑洞同榻而眠。建国以后他多次成为的座上宾,但没接受毛主席让他在政府中任职的建议,又多次提出不同意见,后来就有“廷争面折”的局面。1974年,他发表《我们今天应当如何评价孔子》,反对以非历史的观点评价孔子,反对把与孔子相提并论。梁先生的代表作是《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国文化要义》等,他的哲学是文化哲学、生命哲学、人生哲学。他主要用心于人生问题与中国问题,为此而思考与行动了一生,其哲学与他的生命融合在一起。
熊十力先生(1885年-1968年)与梁先生一样,也参加过辛亥。他原名子真,湖北黄冈人,是一位传奇式的人物,从没有受过任何旧式与新式教育,只读过半年私塾。他生长在贫瘠乡间的一个贫苦农家,幼时为人牧牛。16-17岁时游学乡间。不久,他与同道受到维新派影响,欲物色四方豪杰,共图天下事。为“运动军队”,他投身行伍,又考入湖北新军特别小学堂为学兵,宣传,联络同人。他加入日知会,并发起组织“黄冈军学界讲习社”,主持该社的活动。他曾参与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运动,目睹鼎革以还,世风日下,“党人竞权争利,终无善果”,痛惜“党人绝无在身心上做工夫者”,深感“革政不如革心”,遂慨然弃政向学,研读儒佛,以探讨人生的本质、增进国民的道德为己任。这是熊十力一生中重要的转折。他曾自谓:“决志学术一途,时年已三十五矣,此为余一生之大转变,直是再生时期。”熊十力早年就有佛学的“天上地下,唯我独尊”的意识。他是自学成才的,特别有天赋,有悟性。

熊十力先生是一个怪才,他从他的老师欧阳竟无先生那里走出来,批评佛教唯识学,创立了融会儒佛的“新唯识论”的哲学体系。抗战时期,熊十力入川,颠沛流离,生活拮据。他凭着对国家、民族、人民和传统文化执着的爱,自甘寂寞,乐以忘忧,勉力著述讲学。熊氏哲学体系之充实、发展、完善并在国内哲学界产生一定影响,亦是在抗战期间。抗战末期出版的《新唯识论》语体文本和《读经示要》是他的思想成熟、体系完成的标志。
孔子基于上天不会丧失掉华夏斯文的信念,自觉身系斯文之传的使命,一身系文化神州之安危,是文化托命之人。熊十力先生30年代在北平居住时,曾自题堂联:“道之将废矣,文不在兹乎?”熊先生以“上天将斯文属余”的气魄,承担着中华文化的慧命。

马一孚
马一浮先生(1883年-1967年)是一位大名士,大隐者,大儒,理学大师,又是著名的诗人与书法家。他早年到美、德、日游学。他是绍兴人,长年隐居杭州。抗战军兴,才出山讲学,他随浙大迁居江西泰和、广西宜山,讲学的内容后来编成《泰和会语》、《宜山会语》。1939年,马先生到四川乐山创办复性书院,有《复性书院讲录》6卷。马先生认为,六经可以统摄一切学术。马先生的儒释道的学养特别深厚,佛学造诣颇深,对宋明理学也有精湛的研究。
抗战时在后方,蒋中正常常召见一些学者去谈话,冯友兰先生、贺麟先生等都分别去见过蒋,据说这都是陈布雷的安排。马先生见蒋是在抗战初,办复性书院之前。据说马向蒋讲两个字:“诚”、“恕”(一说为“虚”)。他希望蒋“恕以接人,诚以开务,以国家复兴为怀,以万民忧乐为念”,强调“诚即为内圣外王之始基”。据说蒋对这种劝诫甚为不快。事后,友人问马先生对蒋的印象,马的评价很有趣,他说蒋“英武过人而器宇褊狭,缺乏博大气象”,又说蒋“举止过庄重,杂有矫揉”。他评价蒋是“偏霸之才,偏安有余,中兴不足。比之古人,不过是刘裕、陈霸先之流人物”。这个评价是很确当的。大家知道,刘裕是南朝宋齐梁陈的宋的建立者,即宋武帝,虽代晋称帝,但没有统一中原。陈霸先是南朝陈的建立者,即陈武帝。这两个王朝都是短命王朝,都没有完成统一大业。大概从心胸、气度和霸业上看,蒋不过是宋武帝、陈武帝之类人物,后来的历史果然验证了马先生的判断。
三先生的交游
1919年,熊十力执教于天津南开学校,教国文。这年暑假之前,熊先生曾写信给当时任北京大学讲师的梁漱溟先生,大意是说:你在《东方杂志》上发表的《究元决疑论》已经拜读,其中骂我的话却不错,希望有机会晤谈。梁先生1916年发表的《究元决疑论》的第三部分,对熊先生1913年在《庸言》上发表的《健庵随笔》批评佛学的看来提出批评,认为熊氏不了解佛学的真义,恰恰是使人有所依归,不致流荡失守。暑假,熊氏由天津到北平,借居广济寺内,与梁先生讨论佛学。两人一见面就畅谈起来,但因看法相左,均未能说服对方。这是一次历史性的会见,此后梁熊二先生交游了近半个世纪,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梁先生此时劝熊先生好生研究佛学。
1917年10月,梁先生就任北大教习,就任时即向蔡元培申明:“我此来除替释迦、孔子发挥外,更不作旁的事。”1919年,梁先生的《印度哲学概论》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次年,他的《唯识述义》(第一册)由北大出版部出版。1920年暑假,梁先生赴南京访学内学院(筹备处),求教于欧阳竟无大师,并介绍熊十力先生入院求学。暑假过后,熊先生没有再去南开教书,而是由德安去南京内学院学习佛法。从1920年秋至1922年秋冬之交,熊先生一直在欧阳竟无先生门下学佛。
1922年秋,在北京大学讲授佛教唯识学的梁漱溟先生顾虑自己学养不足,恐怕有无知妄谈之处,征得蔡元培校长的同意,代表北大专程去南京内学院聘人。梁先生原意是请吕澂先生来北大讲佛学,但欧阳大师不放,遂改计邀熊十力先生北上。蔡先生很尊重熊先生,他们在进德会时期有过交往。1918年,蔡先生为熊先生的作《心书》写过序。由于蔡校长十分看重熊十力的德行与才气,熊先生这位既无学历又无文凭的人,被北京大学聘为特约讲师,主讲佛教唯识学。这年冬天,熊先生到北大任教。
在北京大学“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学术环境中,熊十力如鱼得水,获得了与学术界精英砥砺学问的机会。正因为有了这一机缘,熊十力才逐步走上了“成一家之言”的道路。
熊十力在北京大学讲授法相唯识之学,边写讲义边讲。原来的讲义基本上依据佛家本义,忠实于内院所学。熊先生从唐代著名佛学理论家玄奘、窥基,上溯印度大乘佛学宗师无着、世亲、,清理唯识学系统的脉络,揭示其理论纲要。
熊十力是一位有创造性冲动的人。这一年,忽然怀疑旧学,对过去所相信和撰写的东西,感到不安,把前所写稿毁掉,而开始草创《新唯识论》。也就是说,在他的《唯识学概论》刚刚印出不久,他已决心自创新说,扬弃旧稿。
1924年熊先生为自己更名“十力”。“十力”是佛典《大智度论》中赞扬佛祖释迦牟尼的话,比喻佛祖有超群的智慧、广大的神通和无边的力量。夏天,梁漱溟正式辞去北大教习,应邀到山东曹州创办曹州高中。熊先生亦暂停北大教职,随同前往。同行的还有他们在北大的学生陈亚三、黄艮庸,四川高节的王平叔、锺伯良、张俶知及北师大的徐名鸿等。他们共同办学、读书、讲学。熊先生参与其事,任导师。梁、熊诸先生对当时学校教育只注意知识传授而不顾指引学生的人生道路十分不满,向往传统的书院制,师生共同切磋道德学问。梁先生实践古代“办学应是亲师取友”的原则,不独造就学生,还要造就自己,这种精神深获熊先生之心。熊梁先生与们一起组成了一个文化共同体。此时熊先生深感以来,唾弃固有学术思想,妄自菲薄,甚非自立之道。
1930年,熊十力在杭州知道有一位马一浮先生是当代国学大师、诗人、书法家,隐居不仕。听说了马先生的颇具传奇色彩的经历,特别是得知马先生的佛学造诣很深,熊先生极想与马先生晤谈。熊十力请原北大同事、时任浙江省立图书馆馆长的单不庵先生介绍。单先生感到很为难,因为马先生是不轻易见客的。从前蔡元培校长电邀马先生去北大任教,马先生曾以《礼记·曲礼》中的“礼闻来学,未闻往教”八个字回绝。熊听说后思慕益切,于是将自己在原唯识论讲义基础上进一步修订、删改成的《新唯识论》稿邮寄给马先生,并附函请教。邮寄后数星期没有消息,熊先生感到非常焦虑和失望。
一日,忽有客访,一位身着长衫、个子不高、头圆额广、长须拂胸的学者自报姓名:马一浮。熊十力大喜过望,一见面就埋怨马先生,说我的信寄了这么久,你都不来。马先生说,如果你只寄了信,我马上就会来,可是你寄了大作,我只好仔仔细细拜读完了,才能拜访呀!说后二人哈哈大笑起来。此后,马熊二先生成了好朋友。熊先生后来修订《新唯识论》(文言文本)的末章《明心》章部分,吸收了马先生的许多意见,在心、性、天、命、理等宋明理学范畴的解释上,受到马先生的影响。1930年11月,马熊二先生往复通信数通。北京大学研究院院长陈大齐(百年)先生聘请马先生为研究院导师,马先生推举熊先生去作导师。他们二人都未去,但相互尊重之情谊甚为深厚。熊先生让李笑春给马先生送去《尊闻录》,马先生阅后,特举“成能”、“明智”二义加以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