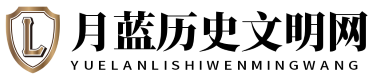小森阳一夏目漱石与二十一世纪
我们可以追朔回顾的“20世纪”常常是把“个人”隶属于“国家”“世界”之名,遮蔽了理应被追究的伦理性。这一隐蔽工作,在“世界史”“日本史”的物语述当中表现最为充分。

(作者:小森阳一,东京大学研究生院综合文化研究科教授)
一、从“帝国时代“到帝国主义”
在19世纪结束20世纪开始之际,一位叫夏目金之助的日本人来到了日本外部的伦敦。在19世纪称霸世界的“大英帝国”的首都的亲身体验虽属偶然,但在思考他的人生经历来说,确实是一个重要的关节点。在此时此地所构想的《文学论》的序言里,他对“汉学里的所谓文学”与“英语里的所谓文学”(这里指的是literature——译者)的决定性的差异的意识,使他下决心要对文学本体论进行彻底究明。因此,对于夏目金之助来说,对“文学”的认识与他对世界的认识的转换具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为何这么讲呢?所谓“汉学”乃是一贯支配亚洲诸地域的帝国“中国”用汉字、汉文书写的知识的遗产的学问。即或它的支配民族地位已发生变化,但是“汉学”仍然盛传不衰,汉学是围绕汉字、汉文书写的知识的遗产的学问,在近代由于西方列强的侵略而衰败之前的清帝国确立下来的训诂考证学,曾经把自己置于“帝国”文化圈内的日本作为核心的学问来对待的儒学均为汉学。与此相对应的英语,在1840年(天宝十一年)西方在鸦片战争中以武力使清朝屈服迫使其开通口岸,进而在1877(明治十年),英语又成为大英帝国吞拼印度帝国(原文如此——译者)后的圈内流行语言。它也是大约在百年前,与“大英帝国”进行武装斗争而取得独立,与英国比肩而立,迫使日本开放口岸的美国也流通的“世界”语言。
“世界”的构图已经从“帝国”时代进入“帝国主义”时代,在这巨大的转换当中,曾几何时属于“帝国”的“清国”文化圈的日本在日清战争(甲午战争)中虽然取得了胜利,但是由于“三国干涉”,对此不能不作出让步,作为欲与西方列强平起平坐,旨在挤进“帝国主义”的日本所派遣的赴大英帝国首都伦敦的这名男性官费留学生夏目金之助,就是在不断崩溃的昔日的国际性体验中,思考都冠名以“文学”的同物的异质性。同时,他还把作为构建国家的民族性-身份的德国的民族主义文学置于另一端一并进行思考。
本来,区别19世纪、20世纪年代乃是以的诞生为起源的纪年标志,在西欧教的共同性中,是以百年为单位来纪年的。“世纪末”这一想法本身,只是我们看取西方历法的内面化的证明。
日本的历法是以与天皇年号为区分的纪年方式。19世纪末那年是明治三十三年,20世纪的第一年是明治三十四年,它们是连续的,从“明治”这一时代来说,是不存在什么“终了”观之类的。夏目金之助“恰巧生在明治维新的前一年”(《文艺与道德》,1911年11月10日)他是持有自己时间意识的一个男人。这样的一个男人,对于用“20世纪”时间节点来认识“世界”,表现出的把西方的历史作为普适的时间观念来考虑的想象是持有批判态度的。同时他对于“明治”这一闭锁的时间意识也持批判态度。
夏目金之助当然要生存在19世纪和20世纪之间的“明治”时代,漱石进行言说的过程中,在那里体现的两重化现象的动态,大概也成为在21世纪又是在“平成”年代还健在的我们对于当下历史意识和时间意识的批判吧。
二、”蒸汽“机车的时代
连西洋也没有”“当然日本更没有”,这是漱石本人对于“在小说界的新运动”发出的宣言(《我的〈草枕〉》,《新小说》,1906年9月号)。漱石有意识地为了推出“俳句式小说”这一体裁而写了《草枕》(《新小说》,1906年9月),在这篇小说的将近结尾处,作为叙述者的画师突然谈了自己的“20世纪”观。从那古井温泉出发,乘坐江船顺流而下到“停车场”刚一到达,画师就以“火车”为题讲了他的“20世纪”观。
我们还是被拽进现实世界了,看得见火车的地方就是现实世界。像火车这样能代表20世纪文明的东西怕是没有了。把几百人一起塞进一个箱子里,轰然奔跑。没有商量。被塞进去的人们以同样的速度拉到同一停车场(此处仍标示了片假名——译者),他们都承受了蒸汽的恩泽。人们叫它坐火车,我把它称作为上货。人们叫坐火车走。我叫它做人被搬运。像这样轻视人的个性之最的东西非火车莫属。文明用尽所有的手段,使得个性发达之后,再用尽其所能的手段践踏个性。给每个人多少平米的地方,不拘你乐意与否就在这里起居生活,这就是现代文明。同时在这多少平米地方的范围再安上铁栅栏,发出的是栅栏里禁入的威吓就是当下的文明。当然栅栏外边是可以自由支配之处,可怜的国民们日夜在这铁栅栏里啃咬,咆哮着。
画师讲的由于“蒸气的恩惠”而开动的“火车”,代表了“20世纪的文明”的见解,是中的之言。如果说以“大英帝国”为开端的西洋的“近代化”=“文明”,最重要的要素乃是产业和世界市场的确立的话,那么使得这两者成为可能的就是“蒸汽”机车。
一般来说,产业是以瓦特等发明的“蒸汽”发动机相伴随的。如果限定在18世纪后半和19世纪初由工业化、机械化而进行的产业资本主义为开拓世界市场而走上舞台,在1830年英国的曼彻斯特通往利物浦的铁路铺设完毕,此后的二十年英国国内的铁路网基本建成。
铁路把首都伦敦和产业城市曼彻斯特、港口城市利物浦连接起来,“火车”在当时首先是装载由工业化机械生产出的商品“搬运”的手段,而非是优先考虑“人”的乘坐。当然,作为岛国的英国从港口城市出发也是用“蒸汽”发动机为驱动,意在支配“七大洋”的英国,利用螺旋桨舰船运送商品,然后从殖民地和外国把原材料、食品等再运回国内。作为“世界工厂”的大英帝国就这样打造了“世界市场”。同时再大大提升以铁炮装备在蒸汽轮船上的海军实力,以军事霸权支配世界。这就是大不列颠制御下的和平时代。这就是19世纪。
“沐浴着水蒸气的恩泽”的“文明”把“世界”均质化、同质化、均一化,把所有的差异的契机消解,英国的铁路网的完备,使得在19世纪中期都市和地方的差别,包括食品在内的商品的差价消解。直至风气的信息的差别也在消解。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由“蒸汽船”“蒸汽火车”的力量,造就了“英语”成为流通语言的“世界”的规模化。
“火车”“把几百人塞进一个箱子里去”“以同样的速度向同一个车站”运送过去。(下划线原作者加)在西洋的一个岛国所发生的相当奇特的事态,在被赋予人类社会普遍意义的价值之时,马上为欧美国家仿效,无论在经济、社会、方面,包括文化方面也向均质化方向转向。明治维新政府的“文明开化”的选择,正是瞄准了要与欧美国家“相同”“同水平”“同一性”的体现,“脱亚入欧”的口号不过是将它更为明确化而已。
产业和世界市场形成时期,也是在法国大提出的“自由、平等、博爱”理念的基础上,布尔乔亚把“个人”“个性”的平等主义结合在一起,与土地私有制为前提的“个人主义”产生的年代重合在一起。由“平等”的个人以自由意志建构的契约社会,就是当初的“国家”的理念。当然,这种“国家”并非露骨地体现出抑压、支配,“给每个人多少平米的土地,在这范围内起居随意”,固然建立在没有限制的个人自由的基础上,好像完全中规中矩的姿态。
但是一旦这一契约刚刚成立,“国家”旋即开始向个人抑压和规限他的自由,保卫“国家”的“国民军”以国家意志来掌控“个人”的生死。立足于扩大市场的资本和国家意志驱使个人与他国进行战争。因为是“给与每个人多少平米的土地”的私有制,为此列强就要扩大土地,以殖民地的手段分割世界。
那就是“帝国主义”战争。漱石在车站看到了包括久一在内的很多出征士兵塞在车里,很快就会再塞进蒸汽船里,把他们弄到日俄战争的战场上去。这就是当今的明治国家在过去的“四民平等”的口号下由“”所实现的东西。
在某种意味上,“文明尽其所有手段,在使个性发展起来之后,再尽其所有手段践踏个性”这样的认识乃是在产业与世界市场形成之时,与之连动进行“帝国主义”战争和民族主义的悖论。“在多少平米”的土地范围之内,在这当中的自由,只不过是限定在内部的铁栅栏的威吓下的保证而已。“20世纪”的“文明”象征的“火车”,首先是在19世纪确立,在20世纪急速推向世界“国家”的国家权力与个人关系的体现。《草枕》里的画师看到的正是这一点。
漱石的论述对于“代表20世纪的文明”的“火车”一直持有异议。人们想的是“乘坐火车”,可是实际上是“被塞进去”;想的是“坐火车奔跑”,实际上是“被搬运”。自己想的是“随心所欲的自由”,实际上“都是被安排的”。是能动的行为活动,实质是在不知不觉间被另外的主体掌控进行被动的行动。“火车”被想象成为具有“主体性”和“自发性”,其实它只不过是被无意识的构造和共同体系所规限的装置而已,这是再明白不过的了。或许画师的“写生文”观点,乃至于“俳句式小说”谭,也是对于这一事态、现象得以超越地看取实质进行批判的场。
“火车”是体现产业资本主义与国家以及使之形成的“20世纪”的“世界”的表象。在写作《草枕》的那一年的一月,漱石在《帝国文学》(1906年1月号)发表了短篇小说《趣味的遗传》,小说写了在“新桥”“车站”从日俄战争中“凯旋”的“将士们”下火车的场景。作为叙述者的“我”写道:当将军下了车后,面对将军爆发出的“万岁”声,听到的是“满洲战场的呐喊的反响”不绝于耳。通过“将军的被阳光晒得黧黑的面容和霜染须鬓”表达的是“战争的结果——确实是结局的一面,而且也有表现活动的结果一面,在一瞬间从眼底掠过,但是就是这一风景让脑海里描画出披着光环诱人的满洲战野的光景。”“我”是如此书写的。“我”是一个“没有亲眼目睹”战争的人,或者说是一个“闲适”的人,但是“无意之中在车站邂逅这样混杂激越的场面”“在映入眼帘的”一幕,在脑海里呈现的是“大战场的光景”“火车”的“车站”也成为和我不期而会的“战争本身的实体”的现实。
还有在《三四郎》(1908年9月1日—12月29日)里写道:在去往东京的“火车”里遇见的在名古屋经过一夜同屋而后分手的那位“火车女孩”只是留下了“你真是个没有胆量的人啊”之后悄然离去。“火车女孩”对于三四郎的意识(作为假象的既存的意识形式)没有抓到,唤起的是日俄战争后“女性”的现实。当然还有很唐突出现的“火车上的女人”的影子中还有一位“火车女性”,在野野宫的住处附近被火车轧死的“从右肩到乳下拦腰一碾而过,抛下斜切下来的半截身子”的被火车轧死的女性的影子,被作者封印在文本里。这一女性也背负着日俄战争后的背景,她们的共同的问题包括那位里见美弥子也具有,对此三四郎是没有意识到的。
还有伴随“火车”出现的东京街道的网络化的城铁和电车,在小说《门》里(1910年3月1日—6月12日)展示了宗助的日常性与“另一个”相邻接的“可能的世界”(休息日的电车、从公署早退时的情景)。在《到彼岸》(1912年1月2日—4月29日)的敬太郎在复杂交错的电车“停留所”被给予一个排除掉作为假象的一切认识形式的手段去识别一名男性的表象的课题。正因为“火车”越是成为作为无法象征的实存的“20世纪”的结构与系统的表象,《到彼岸》的须永和《行人》(1912年12月6—13年11月15)的三泽不管是不是人为的系统均无视意愿地规拘着人们,他们都是抢到列车时间表等车的间隙,进而像是从这一系统中找回自己的主体,在“车站”等待火车的时间里和友人进行对于这个自我的告白。当然,对于这位“我”的告白对于须永来说是千代子、三泽是以述说发疯的“女儿”来体现的。
正因为如此,《心》(1914年4月20—8月1日)的“我”利用“车站的墙壁”上给母亲和哥哥写封家书,告诉他因为去先生家而没有赶上在父亲去世前见最后一面的原因。“断然地奔向开往东京的火车”在“呼隆呼隆作响的三等车厢里”把“先生的信”从头到尾读过。当然作为我们读者来说,读“先生”的遗书的时间,在小说里是与“呼隆呼隆作响的列车”的时间重合的。在那里,是先生必须健在时的“我”和当下这位青年“我”的会面。
“漱石”的“火车”实际上是让“我”与我两个主人公同乘的。
三、”个人“的时代
“不乘坐火车,也不坐马车,胡乱地利用交通工具的话不知道会把自己拉到哪儿去。对于“在密集如网的道路上往来的火车、马车、电车等一概拒绝”的这位《伦敦塔》(1905年1月)里的叙述者,那位住在伦敦的日本的一名留学生颇像“我”。“我”通过《伦敦塔》作了超越“20世纪”的发现。
“遮蔽过去这一怪物的帷幔自己裂开了,关注的幽光在20世纪上面作了反射。”这就是《伦敦塔》,“它以轻蔑的眼光对待20世纪”看了《伦敦塔》之后,就会觉得”20世纪的伦敦在我们心中会逐渐消失。
以“漱石”为署名作者的叙述起始而于《猫》,《猫》旨在于让生活在20世纪的人们挣脱出来,进入体现过去的《伦敦塔》之中去,和它同化,一起“蔑视20世纪”。但是无论是“猫”还是“我”都无法超越20世纪。不,也许正是为了写出这一点而选择“猫”和“我”吧。
在一定的意味上,漱石是拒绝浪漫主义的超越。正如“猫”绝不允许朝着上流社会的超越,在《塔》里的“我”也是被拉回到现实中来。这一现实经验是他者反复处理之后的信息。并非超出预想.
“这是当然的了,诸位想到哪去的话就先看看导游介绍好了。”“20世纪的伦敦人”如此谈话,出门前一定要读旅游指南。如果事先不如此就不能出门。这就是生活在20世纪伦敦”的“诸位”的生活方式。他们的所有的经验均出自于模仿某种言说化的信息,这种情况是“理所当然的”。这就是“20世纪”。把它叫做模仿也可,或者说成用媒介作为中介也可的的转让也可。但是这不是问题所在。重要的是,“轻蔑20世纪”即使想把它“抹消掉”,但是“还是又返回到了20世纪”,漱石的言说是以此为出发点的,对此非常自觉。
同时《塔》和《猫》作为互为表里的作,超越这一状况是不可能的,虽然对此心知肚明,但是对于这一状况仍然进行批判,这一点可以说这是饶有意味的。
称作“20世纪”的“世界”的共同性,以及支撑它的体系对此以身相许,如此一来主体就被这一体系转卖了。那么这一主体如何被如回复呢?应该说在主体返回前是如何存在的呢?我们不妨再次回到《草枕》的文字。
文明给个人以自由犹如使之变成猛虎,之后就要把他关进笼子里,来维持天下的和平。这一和平并非是真正的和平。动物园的老虎盯视着观看它的游客,仍然在那里躺着,同样也是和平。如果拔下虎栏的铁栏杆——世界可就一塌糊涂了。第二次法国就可能在这种情况下发生吧?个人的如今在日夜进行着。北欧伟人易卜生就是对于这必然发生的给我们拿出了具体例证。我看到火车如此威猛,没有界限的,把那么多的人象货物一样随心所欲地拉着奔跑的样子时想到被圈在客车笼子里的个人,火车是毫不在意什么个性的。——两相比较后——感到可怕。非常可怕。不注意这一点的话是很危险的。现代文明就是充斥在你面前的危险。朝着一片昏暗的前方盲动的火车就是一个标本。
画师在认识上重要之点在于:一、到达“20世纪”之时的“个人”乃是由文明打造形成的,这个“个人”被给与的自由,也是由“文明”所赋予的。同时在先前引用的部分里,主语也是文明。进而可以说,构建之个人,换言之,通过“文明”所产生的主体,并非是个人,是以文明的形式不断以画师的言说得以不断构建出来。假如立足到“代表”这一“文明”的“火车”的认识的话,会如何表述呢?
有“火车”作为表象的“文明”,肇始于英国,从产业和世界市场的角度来说,从殖民地不断地输入能源和原料,由国内工业制造出商品,再输出到国外,通过差别的利益提高国内生活水准,可以说这就是“20世纪”英国走过的通向“福祉国家”的路径。
这样的“文明”必然首先在殖民地住民中实行,对于被支配的地域的人民来说进行的是压倒性的掠夺和榨取,在由此带来的牺牲和排除的基础上得以成立。如此,建立在此基础上的“个人”与“自由”,就不存在一点什么普适性。为何如此?因为现在所说的这一特殊条件,即英国式西欧式的“文明”如果不完备的话,“个人”“自由”就绝不会成立的。
简要地说,“文明”的发达,掠夺的乃是“个人”与“自由”,由对殖民地的经营而使本国成为“福祉国家”是和国家主义联动,把主体转让给”国家”的欧美人的产物而已。或者说拼力要加入到“帝国主义”阶段的日本人的货色也是如此。
但是,围绕“个人”与“自由”的观念,当它超越了阶级,并且由于业已形成的世界市场的作用成为流布世界的观念,一旦超越了民族和国家,其观念包含的普适性,也将超出把特殊条件一般化、世界化的框架,并且将威胁由此产生过它的文明结构本身。指向这样的“文明”的他者性,或者说寄身于外部的“个人”,就是那只老虎。
把“虎”关在笼子里,即使“拔掉了笼子的一根铁棒”,就会发生“第二次法国”。它绝非是第一次即在现实中发生的法国的重复。为什么呢,这一“”是一次对于隶属于“文明”主体已经主体化的值得同情、“可怜的文明的国民”和在这一文明的铁笼当中的“自由”两方面都要一起进行批判的“”。画师在“易卜生”里看到的也带有这样的批判性。
在“20世纪”被问题化的是自己自觉意识到被关在火车里了,被抹煞种种个性的个人如同货物一样,是被“同一”“一般化”的“个人的个性”,为何以火车为表象的西欧类型的“文明”只能是对于个人的个性丝毫不会注意的“铁车”了。唯此才惊呼“20世纪”“危险,真危险”。
因为并非是在普适的层面上把“个人的个性”问题化,或者说,某种意味上以不发生“个人的”为限,这样一来,西欧性的“个人”就必然沿着与“国家”“民族”保持同一性的中心轴民族主义前行。具有追溯“20世纪”特权的我们,通过两次世界大战,紧跟着的“冷战结构”,接着是前苏联的解体、世界的民族主义动向,都可以看到这一点。
夏目漱石认为那种在西欧类型的基础上形成的“个人主义”,乃是对于更大的主体的隶属化而形成的个人,不曾有一点实际意义。因此漱石的“个人主义”,是与“利己主义”和“个体主义”无缘的。
漱石的《我的个人主义》这一演讲,回顾了自己“自我本位”的成立过程,它对于普适化的西欧型的“个人”是持批判态度的。产生这一批判意识的萌芽阶段,恰恰在20世纪20年代,他在伦敦留学期间,在构思写作“文学论”之时。漱石此时回顾过去
此时我在思考到底文学为何,想到我除了通过这一概念从根本上靠自力自救以外别无他途。至今全是他人本位,好像无根的浮萍,漂泊不定,对此已逐渐感到讨厌。我在这里讲的他人本位这东西很象拿自己的酒让别人喝,过后去听别人的品评。即使对方的品评是错的,也认为就是如此,所谓以他人为准之谓也。(加重点原有,下同)
在这里被批判的是“与人雷同”的“他人本位”,这一问题漱石以喝酒的例子来说明,被作为趣味的领域来对待的,或者说,趣味和在原理上来说是相当独立的领域,指的是在趣味和上也模仿他人。
当然我们要提出鲁内•吉拉尔的《现象学》,其对“他人本位”的批判必然是对于“近代个人主义”,或者说与它互动的浪漫主义的批判。模仿他人的趣味与的“主体”,只能是隶属于他者的主体化的存在而已。这种存在方式只能为“他人本位”。为此,在如下的地方说日本人对于西洋人的独立,看作为民族主义的言说的“主体”的话,漱石批判的只能是“他人本位”。
举例子来说,西洋人说这是一首好诗,即使态度非常喜欢,这也是西洋人的视点,即使不令其作为我的参考,假如我不是那样想的话,终究在我这里不会接受。我是一个独立的日本人,绝非是英国人的奴婢这一见识作为国民的一员是必须具备的。就是从必须具有的世界共通的正直的道德观来说,我也不能违心求同。
在此成为问题的是“我”对于诗的评价的好恶与趣味判断问题。正因为是在“英文学”领域,才进行“西洋人”和“我”的比较,置言之,已经是一定的趣味判断的积累成为既存的模式,因此使之和“我”进行对比。同时强调在“国民”这一层面上,“日本人”没有成为“英国人”的“奴婢”的必要。对于“我”来说重要的是正直的“世界共通的道义观”里,我自己的独立的意见不能被扭曲。
换言之,这一特殊化绝非是不能一般化意味上的特殊化,那是单独的“我”立于自己的立脚点与趣味判断之上而形成的问题意识。同时这一“单独性”的问题被置于“风俗、人情、习惯并上溯到国民的特点”的各个层面的存在上来被加以强调。对于把某一特殊性当中产生的东西使之一般化,对于进而使之进行普适性包装的“正宗”批评家们,就和仅以单独性作为存在的“我”形成对置。
在这一意味上的“我”,不仅是面对“西洋人”“英国人”的存在,对于日本人来说也是单独的人,即使在现在,能够提供某作家本身的独特的作品评价的英文学者或者说外国文学研究者,在“日本人”当中还相当少见的。
《文学论》“正是为了给自己本位立证的科学的研究与思考”而进行的反复的积累的成果。作为本人来看的话,“《文学论》毋宁说是失败的残骸远远大于它的值得纪念的意义。”而且,是一个畸形儿的残骸。“‘自己本位’四字”使得伦敦的夏目金之助更为强势,为此“这一新的方法”得以出现。
如此的“自己本位”,即“自己想的喜欢的事情、合乎自己天性的事、又很幸运地能使自己沿着自己的个性得以发展的方向前行。”“理所当然”对于他者的他者性,即他者的“自我本位”给予承认,由此自己本位得以成立。漱石在演讲中向听众发出对于通过“他者本位”以权力、金钱来压制别人,占据这一位置有这种可能性的精英们保持高度的警惕。
立于自己的和趣味,不去找寻其他一切根据,让这单独性合理的生存。即使是毫无根据的单独性,也可以窥见到普适的东西。《文学论》的主旨即在于此。当然这种普适性的东西并非以实体而存在。
立于这一理论层面的漱石说:“我可以说也是国家主义、世界主义,同时又是个人主义。”在这种态势下,“国家”“世界”“个人”、并非相互隶属,或者说也不应使之相互隶属,是层面不同的主体。立于这一观点,它与单独的中庸论具有相当差异的理念,又体现了笛卡儿的主体论、国家论、世界论的东西。
为了获得自己单独的自由,只能保证他者的在他自身的自由,这一认识作为“当然之理”在个人层面上,在“道德”“伦理”的层面上,产生出高于“国家”的议论。为何如此呢?因为伦理性问题从最根本的方面来说,是建立在相互单独的或者说是毫无共有关系的两者的关系上的,这是立于人类行为的场。
从这一意味上来说,我们可以追朔回顾的“20世纪”常常是把“个人”隶属于“国家”“世界”之名,遮蔽了理应被追究的伦理性。这一隐蔽工作,在“世界史”“日本史”的物语述当中表现最为充分。在“”这一场里,如今仍在实行的用“国际贡献”的口号,日本作为从属于美国的“国家”的权力和“财力”的方向都被包装、隐蔽起来。对于被遮蔽的伦理性发出重新质疑的话语,作为个人存在的小说家,到作为个人存在的读者手中,这一言语装置只是一种虚构。漱石所说的“个人主义”在21世纪的当下,其思想的重要性仍然没有失去。
人学研究网·人类通史栏目责编:童心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