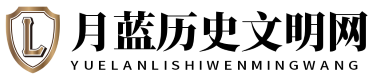南北朝无神论的战斗传统
《神灭论》是用问答体,一步深一步地阐述自己的观点,一方面继承了汉王充自然哲学的传统,另一方面也吸收了魏晋以来名理辨析的续余。

佛教和道教的广泛传播,有助于封建朝廷对人民的精神统治。但佛、道之间有矛盾,佛、道跟统治者之间也有矛盾,甚至出现了封建朝廷对佛、道进行毁灭性的打击。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无神论者对于鬼神及成佛成仙的虚构,进行了揭露和批判,这是无神论的战斗的优良传统。
中国佛教史上有所谓“三武”的灭佛活动。第一次是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太平真君七年(446)的灭佛。拓跋焘于太平真君五年(444)曾下诏,禁止王公以至庶人私养沙门、师巫。沙门是佛教中人,师巫应是道教中人,这似是佛、道并举的。到了太平真君七年,拓跋焘下诏,坑杀全国沙门,烧毁所有佛像。因为事先走露风声,有些僧人得以逃遁,没有全部被杀。第二次是北周武帝宇文邕建德三年(574)的灭佛。这次灭佛,是经过朝廷上的多次议论,最后才决定了的。宇文邕的诏书,是禁断佛、道之教,实际上是针对着佛教,想把三百万僧人收为编户,四万所庙宇收归官府。这对于调整农民的劳役和租税的封建负担,都有一定的好处。在这次灭佛之前,北齐文宣帝高洋天保六年(557)还曾下令禁绝道教,要所有道士削发为僧,不从者立即斩首。如道士自称是神仙,就命他从铜雀台上跳下去,粉身碎骨。以上两次灭佛和一次禁道,都反映统治阶级内部之不同形式的斗争。但无论灭佛或禁道,都是暂时性的,对佛、道的尊崇则是经常性的。后来还有第三次的灭佛,那是在会昌五年(845),是唐武宗时的事了。北魏北周的灭佛,和北齐的禁道,都是以暴力强迫进行的活动,谈不到无神论对有神论的斗争。这是北朝反佛、道活动的特点。南朝跟北朝不同,从宋到梁,有神无神、神灭不灭的论争不断。这种论争,是中古社会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间论争的一种特殊形式。范缜是南朝反对有神论的旗手,他
的《神灭论》是震撼当代思想领域的唯物主义的杰作。在他以前,有孙盛、何承天、范晔,与他约略同时的刘峻,都是阐扬无神论的学者,也都是南朝的人物,而孙盛、何承天、范晔又都是历史学家,刘峻也是博通文史的人。
孙盛(302—373),东晋太原中都(今山西平遥西南)人,官至秘书监。着有《魏氏春秋》、《晋阳秋》。《晋阳秋》记晋枋头之败,触怒了桓温,并受到威胁。孙盛坚持照实记载,不肯迎合权势。当时,有罗含着《更生论》,认为“万物有数,而天地无穷”,“万物不更生,则天地有终矣。天地不为有终,则更生可知矣”。他由此推论,认为神之不可灭,“聚散隐显,环转于无穷之涂”。孙盛给罗含书信,称:“吾谓形既粉散,知[神]亦如之,纷错混淆,化为异物。各失其旧,非复其旧。”这是指明,形体既已不存,精神也随之消散。孙盛是以神灭思想批判罗含的神不灭思想。
何承天(370—477),宋东海剡(今山东剡城北人。官至国子博士,御史中丞。他精于天文历算之学,宋初撰定《元嘉历》。又受诏撰《宋书》,草立纪传,止于武帝功臣。志,原定十五篇,他写出了一部分,其中包含《天文》、《律历》。后来沈约修定的《宋书》,对他的旧稿多所因袭。此外,他还着有《春秋前传》和《春秋前杂传》,并删定了《礼论》三百卷。与何承天同时代,有宗炳者,着《神不灭论》,宣称“精神不灭,人可成佛,心作万有,诸法皆空。宿缘绵邈,亿劫乃报。”并称,“夫精神四达,并流无极,上际于天,下盘于地”,形虽灭而神不灭。何承天给宗炳写了一信,直接驳斥宗炳的这种观点。他指出,“形神相资,古人譬以薪火。薪弊火微,薪尽火灭。虽有其妙,岂能独传”。并着有《达性论》,驳斥佛教的轮回之说。他指出:“生必有死,形毙神散,犹春荣秋落,四时代换,奚有于更受形哉?”他又着《报应问》以驳斥佛教因果报应之说。他指出,鹅浮游于池塘,与人无争,而难免于庖人的刀俎;燕以昆虫为食,却得到人们的爱护,“是知杀生者无恶报,为福者无善应”。何承天以生活中习见的事例进行论战,说理虽简单,却使对方难以辩解。
范晔《后汉书》的作者,与何承天同时代人。他“常谓死者神灭,欲着无鬼论”,但没有写出来。他因事被株连,临刑前还“语人寄语何仆射(何尚之),天下决无佛鬼。若有灵,自当相报。”第二句是讽刺何尚之,意思似是说,如何尚之真是心口如一地相信因果报应之说,就不会诬陷人了。
范晔在《后汉书・西域传・论》里,比较集中地批评了佛教。在一开始,他指出自张骞以来对西域的记载“莫不备写情形,审求根实”,但都没有写什么印度佛教的神话。后来关于佛教“理绝人区”的“神迹诡怪”和“事出天外”的“感验明显”等等,都是张骞、班超没有听见过的。范晔问道:“岂其道闭往运、数开来叶乎?不何诬异之甚也!”这是要从历史上指出佛教的种种说法都是后起的,因而与张骞、班超所记的相比,就显得有很厉害的虚构和怪诞了。下文说:详其清心释累之训、空有兼遣之宗,道书之流也。且好仁恶杀,蠲敝崇善,所以贤达君子多爱其法焉。然好大不经,奇谲无已。虽邹衍谈天之辩,庄周蜗牛之论,尚未足以概其万一。又精灵起灭,因报相寻,若晓而昧者,故通人多惑焉。
范晔在《后汉书・桓帝纪・论》里说:“前史称桓帝好音乐,善琴笙,饰芳林而考濯龙之宫,设华盖以祠浮图老子。斯将所谓听于神乎!”他在这里用了《左传》上的一个典故,批评了汉桓帝崇佛的荒谬。他在《襄楷传》收入襄楷上桓帝书:“闻宫中立黄老浮图之祠。此道清虚,贵尚无为,好生恶杀,省欲去奢。今陛下嗜欲不去,杀罚过理,既乘其道,岂获其祚哉?或言老子入夷狄为浮屠。浮屠不三宿桑下,不欲久生恩爱,精之至也。天神遗以好女。浮屠曰:此但革囊盛血,遂不盼之。其守一如此,乃能成道。今陛下艳妇,极天下之丽;甘肥饮美,单天下之味。奈何欲如黄老乎?”这篇上书之收入《后汉书》,可看作是范晔对崇佛的“贤达君子”的讽刺。这些人也只是嘴上说说佛法,在实际生活上是不可能遵从佛教戒律的。
刘峻(462—521),字孝标,原籍平原(今山东平原县南),父亲流寓江南。他经历了大半生极为坎坷的生活,晚年居东阳(今浙江金华县)讲学。他着《辨命论》指出:“夫通生万物,则谓之道:生而无主,谓之自然。自然者,物见其然不知所以然,同焉皆得,不知所以得。鼓动陶铸而不为功,庶类混成而非其力,生之无亭毒之心,死之岂虔刘之志,坠之渊泉非其怒,升之霄汉非其悦。荡乎大乎,万宝以之化:确乎纯乎,一化而不易;化而不易,则谓之命。命也者,自天之命也;定于冥兆,终然不变,鬼神莫能预,圣哲不能谋,触山之力无以抗,倒日之诚弗能感,短则不可缓之于寸阴,长则不可急之于箭漏,至德未能逾,上智所不免。是以放勋之世,浩浩襄陵;天乙之时,焦金流石;文公嚏其尾,宣尼绝其粮,颜回败其丛兰,冉耕歌其芣苡,夷叔毙淑媛之言,子舆困臧仓之诉,圣贤且犹若此,而况庸庸者乎?……咸得之于自然,不假道于才智。故曰:‘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其斯之谓矣。”刘峻认为,一切都成于自然,所谓“道”、“天”、“命”,都是“自然”的同义语。“自然”的背后,别无主宰,人的才能贤愚在这里一点力量也用不上。这是跟有神论相对立的思想。这说的是一种机械的必然法则,并带有命定论的性质。但比起过去的一些无神论者简单地从个别自然现象或个别社会现象立论,在理论上有了发展。
范缜(约 450—515),字子真,祖先原籍顺阳南乡(今河南浙川县),东晋初年流寓江南。他早年从名儒刘 学习。史称他“博通经学,尤精三《礼》。”南齐时,司徒竟陵王萧子良开西邸,延致宾客,范缜也是被延揽的宾客。萧子良信佛教因果报应之说,而范缜不信。子良问:“君不信因果,世间何得有富贵,何得有贫贱?”范缜答:人之生,譬如一树花,同发一枝,俱开一蒂,随风而堕,有的是落在茵席之上,有的是落在粪土之侧,这只是偶然的遭遇,贵贱因而不同,因果究在何处?子良没有能说服他。
范缜着《神灭论》,这是他反佛的杰作。《神灭论》跟佛教信徒的神不灭论的根本分歧,在于范缜坚持“形神相即”,而后者则宣扬形神相异。范缜所说“形神相即”,用他的话说,即“神即形也,形即神也,是以形存则神存,形谢则神灭也。”从事物之总的方面说,形神是统一的,不能分割。从形神的关系说,神的存灭从属于形的存谢。这是旗帜鲜明的唯物的一元论。神不灭论者所宣扬的形神相异,其主旨在于强调神的独立存在,神可独立于形之外,形灭而神不灭。这是以形从属于神,也是佛家轮回说的理论依据。范缜更申论形神的关系,说:“形者,神之质;神者,形之用。”这是以形为神的本质,为神的基础,而神则是形的作用。范缜还以刃与利的关系来说明形神的关系。他说:“舍利无刃,舍刃无利。未闻刃没而利存,岂容形亡而神在?”《神灭论》是用问答体,一步深一步地阐述自己的观点,一方面继承了汉王充自然哲学的传统,另一方面也吸收了魏晋以来名理辨析的续余。
《神灭论》出,“朝野喧哗。子良集众僧难之,而不能屈”。子良又派人以相诱。范缜大笑,表示不能“卖论求官”。梁武帝即位第三年(504)诏:佛教以外,都是邪道,百官王侯都要“舍邪入正”。后来,梁武帝降敕,不点名地指斥范缜“违经背亲,言语可息,神灭之论,朕所未详”。大僧云,还在这时鼓动王公朝贵六十二人,以信札的形式对范缜围攻。范缜并不为这些干涉所动摇,仍坚持神灭的理论,显示了一个唯物主义思想家的战斗精神。——白寿彝《中国通史三国魏晋南北朝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人学研究网·中华文明栏目责编:紫天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