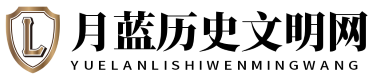刘梦溪中国现代史学人物一瞥
史学在中国自有不间断的传统,由传统史学转变为现代史学,应是顺理成章之事。然而向传统史学置疑容易,提出史学的新概念、真正建立新史学,殊非易事。 (作者:刘梦溪,中国艺术研究院终身研究员、中国文化研究所所长) 现代史学家中包括“二陈”在内的一批大师巨子,所涉猎和所建树的史学实际上也可以视作文化史学。所谓文化史学,是指著者不仅试图复原历史的结构,而且苦心追寻我华夏民族文化传承的血脉,负一种文化托命的职责。 史学在中国自有不间断的传统,由传统史学转变为现代史学,应是顺理成章之事。然而向传统史学置疑容易,提出史学的新概念、真正建立新史学,殊非易事。 现代史学开创者:梁启超、胡适 已故经学史家周予同先生,在1941年写的《五十年来中国之新史学》一文中,有如下的论述:“学术思想的转变,仍有待于凭借,亦即凭借于固有的文化遗产。当时,国内的文化仍未脱经学的羁绊,而国外输入的科学又仅限于物质文明;所以学术思想虽有心转变,转变的路线仍无法脱离二千年来经典中心的宗派。”(见朱维铮编《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第517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事实确是如此。单是新史学与经今文学的关系有所厘清,已是困难重重。按周予同的说法,晚清治史诸家中,崔适、夏曾佑都是经今文学兼及史学。只有梁启超是逐渐摆脱了今文学的羁绊,走上了新史学的道路。 就此点而言,任公先生对现代史学的贡献可谓大矣。而现代史学中的学术史一目,也是任公先生开其端的,《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清代学术概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三书,就是他研究学术史的代表作,至今还经常被学者所引用。诚如梁之好友林志钧所说:“知任公者,则知其为学虽数变,而固有其紧密自守者在,即百年不离于史是矣。”(林志钧:《饮冰室合集序》,中华书局1989年版《饮冰室合集》第一册,第3页)但梁之史学,前期和后期的旨趣不尽相同。 1901至1902年写作《中国史叙论》和《新史学》的梁启超,对传统史学的态度甚为决绝,他总结出旧史学的“四蔽”(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二病”(能铺叙而不能别裁;能因袭而不能创作)、“三难”(难读,难别择,无感触),摧毁力极大。后来写《清代学术概论》、《历史研究法》和《历史研究法补编》,则表现出对传统史学不无会意冥心之处。但不论前期还是后期,梁之史学都有气象宏阔、重视历史整体、重视史学研究的量化、重视科际整合的特点。他把中国历史分为三个阶段:从黄帝到秦统一,为上世史,称作“中国之中国”;秦统一至乾隆末年,为中世史,称作“亚洲之中国”;乾隆末年至晚清,为近世史,称作“世界之中国”(梁启超:《中国史叙论》,《饮冰室合集》第一册,文集之六,第11至12页)。这是一种着眼于大历史的分期方法,颇能反映中国历史演化的过程。 胡适的史学在梁的基础上又有所跨越,《白话文学史》、《中国哲学史大纲》,在专史方面已是开新建设的史学了。但胡适实验的多,完成的少,他的作用主要在得风气之先和对史学研究的“科学方法”的提倡。二十年代兴起的古史辨学派,除了受康有为所代表的晚清今文学的影响,与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直接“从周宣王以后讲起”有很大关系。顾颉刚在《古史辨》第一册的自序里写道:“第二年,改请胡适之先生来教。‘他是一个美国新回来的留学生,如何能到北京大学里来讲中国的东西?’许多同学都这样怀疑,我也未能免俗。他来了,他不管以前的课业,重编讲义,开头一章是‘中国哲学结胎的时代’,用《诗经》作时代的说明,丢开唐禹夏商,竟从周宣王以后讲起。这一改,把我们一班人充满着三皇五帝的脑筋,骤然作一个重大的打击,骇得一堂中舌挢而不能下。”(《古史辨》第一册,第36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所以当1923年顾颉刚在《读书杂志》上发表《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提出著名的“层累造成说”,胡适给予支持;而钱玄同和傅斯年也作有力的回应,疑古遂掀起波澜。顾的“层累造成说”包括三方面的意思: 第一,“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期愈长”。如这封信里说的,周代人心目中最古的人是禹,到孔子时有尧舜,到战国时有黄帝神农,到秦有三皇,到汉以后有盘古等。第二,可以说明“时代愈后,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如舜,在孔子时只是一个“无为而治”的圣君,到尧典就成了一个“齐家而后国治”的圣人,到孟子时就成了一个孝子的模范了。第三,我们在这上既不能知道某一件事的真确的状况,但可以知道某一件事传说中的最早的状况。我们即不能知道东周时的东周史,也至少能知道战国时的东周史;我们即不能知道夏商时的夏商史,也至少能知道东周时的夏商史。(顾颉刚:《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载《古史辨》第一册第60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 这些观点他想在一篇叫做《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的文章中论述,文章未及写,先在致钱玄同的信里讲了出来。倍受争议的禹大约是“蜥蜴之类”的一条“有足蹂地”的虫,就是此信中的名句。 顾的这封信在学术界引起巨大的震撼。他后来回忆起这段往事时说:“信一发表,竟成了轰炸中国古史的一个。连我自己也想不到竟收着了这样巨大的战果,各方面读些古书的人都受到了这个问题的刺激。因为在中国人的头脑里向来受着‘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的定型的教育,忽然听到没有盘古,也没有三皇、五帝,于是大家不禁哗然起来。”(顾颉刚:《我是怎样编写古史辨的》,载《古史辨》第一册第17至18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读书杂志》系胡适主办,因为顾的这封信展开了一场历时个月的大讨论,直到1924年年初方告一段落。而1926年出版的《古史辨》第一册,则是对这场讨论的总结,顾颉刚写了一篇六万余言的长序,“古史辨”作为学派因之而诞生。 当时与“古史辨派”相对立的是释古派和考古派。也有的概括为“泥古派”或“信古派”,指起而与顾颉刚、钱玄同论争的柳诒徵等文化史家,影响不是很大,且用“泥古”或“信古”字样概括他们的观点似不够准确,可暂置不论。考古派首功当然是罗、王、郭、董“四堂”(罗振玉号雪堂、王国维号观堂、郭沫若号鼎堂、董作宾号彦堂),还有李济、夏鼐等。当然考古者大都也释古。董的《殷历谱》和《甲骨文断代研究例》、郭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和《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李济的《中国民族的形成》和《安阳》等,均堪称古文字与古史研究的典范之作。释古派可以王国维和陈寅恪为代表。如果认为梁启超提出的多,系统建设少;王、陈的特点,是承继的多,开辟的也多。 最具现代性的史学家:陈寅恪 特别是陈寅恪的史学,是最具现代性和最有发明意义的中国现代史学的重镇。 他治史的特点,一是在史识上追求通识通解;二是在史观上格外重视种族与文化的关系,强调文化高于种族;三是在史料的运用上,穷搜旁通,极大地扩大了史料的使用范围;四是在史法上,以诗文证史、借传修史,使中国传统的文史之学达致贯通无阻的境界;五是考证古史而能做到古典和今典双重证发,古典之中注入今情,给枯繁的考证学以活的生命;六是对包括异域文字在内的治史工具的掌握,并世鲜有与其比肩者;七是融会贯彻全篇的深沉强烈的历史兴亡感;八是史著之文体熔史才、诗笔、议论于一炉。他治史的贡献,主要表现在对“中国境内之古外族遗文”的释证、对佛教经典不同文本的比勘对照、对各种宗教影响于华夏人士生平艺事的考证、对隋唐制度文化渊源的研究、对晋唐诗人创作所作的历史与文化的笺证、对明清易代所激发的民族精神的传写等等。而所有这些方面,他都有创辟胜解。他治史的精神,则是“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这是他学术思想的力量源泉,也可以称作陈氏之“史魂”。1929年陈寅恪所作《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写道:“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唯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金明馆丛稿二编》第218页)《柳如是别传》之缘起部分也有如下的话:“虽然,披寻钱柳之篇什于残缺毁禁之余,往往窥见其孤怀遗恨,有可以令人感泣不能自已者焉。夫三户亡秦之志,九章哀郢之辞,即发自当日之士大夫,犹应珍惜引申,以表彰我民 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