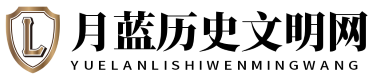张爱玲早年经历导致的悲剧意识
张爱玲创造了一个以苍凉为底色的小说世界,这与她荒凉的精神世界密切相关。令人惊异的是,完成《金锁记》、《倾城之恋》、《桂花蒸一一阿小悲秋》、《红玫瑰白玫瑰》、《沉香屑一一第一炉香》等作品时,张爱玲仅仅只有二十三、四岁。
这些充满了人生悲剧意识(即荒凉感)的优秀作品是那样憾人心魄,它显示了年轻的张爱玲对人生独特而稳定的把握。那么,是什么原因形成了她的悲观气质和创作上的悲剧意识呢?我们不妨从她的人生历程中做一些探寻。

没落的家世,深刻的烙印
张爱玲出身名门望族。祖父张佩伦是满清大臣,清流派名士,祖母李菊藕是李鸿章的女儿,母亲是黄军门的小姐,但却“来的太迟了”,没有赶上家族的“热闹”,只亲身经历、亲眼见证了这个曾经煊赫的大家庭的败落和坐吃山空。
豪门巨族由于时代变迁的没落,对后世子孙的影响是巨大的。显赫的家族已经没落了,遗老遗少们仍然沉迷于过去,力图在家里建立一个小小的王朝,他们的思想感情离现实很远,对现实的不满与拒绝更使他们美化过去。
这种与没落的情调在张爱玲幼年的时候就浸润着她的心。在父亲暮气沉沉的书房里,在有着古墓般清凉的旧宅第中,没落的家族在张爱玲的意识中印上了属于他们的徽章。在晚年出的《对照记》张爱玲这样写道:“他们静静地躺在我的血液里,等我死去的时候再死一次”。
而那种盛极而衰的强烈对比给她的刺激是深刻的,更在她的心灵上投下了巨大阴影。“我三岁时背唐诗。我还记得摇摇摆摆立在一个满清遗老的藤椅前朗吟‘商女不知恨,隔江犹唱**花’,眼见他的泪珠滚落下来”(《天才梦》)。
童年的创伤,最初的动因
张爱玲四岁时候,一直与父亲不和的母亲离家出洋,使张爱玲从小就失去了正常的家庭与温暖,失去了母亲的关爱。幼年生活给她造成了极大的心灵创伤,更不幸的是这创伤没有在少年时代及以后得到修复和补偿,反而加剧了。
父母的离异,继母的,使张爱玲少女时代的家庭生活充满了委屈和难堪。不幸的家庭生活使张爱玲分外敏感、早熟,而这敏感、早熟又使她在那样的生活环境中过早地积累了对人和事的否定性情绪。
这种由童年的心理创伤造成的否定性情绪,便是形成张爱玲人生悲剧意识的最初动因。

冷漠的亲情,自私虚伪的人性
中学毕业时,张爱玲因为母亲的支持向父亲提出了留学的要求,却遭到父亲的一顿毒打,并被关了半年多。“我生了沉重的痢疾,差一点死了,我父亲不替我请医生,也没有药”(《私语》)。
这一次的不幸是张爱玲有生以来最激烈,也最沉重的打击。她不仅对赖以生存的家庭和亲人产生了绝望的感情,而且对自己的生命意义也产生了疑问,对生命的黯淡与苍凉有了更加切实的体验。在长篇小说《十八春》里,顾曼桢被骗后关押的情节,描述的那样真切具体,无不透露出作者自己当年被关押的感受和体验。
逃离父亲后,张爱玲迫不得已地投奔母亲。但母亲在经济上的困窘,并没有使她得到想象中的温暖,她在母亲那里得到的爱也是残缺的。
从童年到青年,母亲总是一次又一次地接近她而又离开她,给予她片刻的温暖又将她扔进黑沉沉的寒夜,这种心灵的折磨是难以言说的。在小说《莱莉香片》里,张爱玲这样写道:“寒天里,人冻得木木的,倒也罢了,一点点的微温,更使人觉得彻骨寒心”。
这样的感受,很难说不是来自张爱玲自己的经验世界,她说“我是一直用一种罗曼蒂克的爱来爱我母亲的……可是后来,在她的窘境中三天两天向她伸手拿钱,为她的脾气磨难着,为自己的忘恩负义磨难着,那些琐屑的难堪,一点一点地毁灭了我的爱。”(《童言无忌》)。
放弃父亲又逃离母亲。再没有别的亲情来填补爱的空白,人不能不孤独,张爱玲在成长的过程中,一步一步地走向了自立,也一点一点地深刻地体验到了亲情的脆弱和人性的自私。
人世间最亲密的亲子关系被撕去了温情的面纱,露出的是自私和冷酷,很难让人对别的感情产生美好的认定,这对形成张爱玲的人生悲剧意识有不可忽视的作用。
“总之,生命是残酷的,看到我们缩小又缩小的,怯怯的愿望,我总觉得有无限的伤惨”(《我看苏青》)。因此,在张爱玲的小说里没有正常的伟大的母爱,更没有父爱。
即使有,也是畸形的一一《心经》里许小寒的父亲对女儿的“爱”让人读了心里不禁生出丝丝寒意;《多少恨》里虞家茵的父亲为了维持自己晚年的放荡生活宁愿劝女儿去做姨太太;曹七巧的母爱是被黄金的枷锁变形了的占有;白流苏的母亲面对了家道的败落,对回娘家的女儿也只能是无奈的敷衍与应付;《琉璃瓦》中的姚先生有七个姿色各异的女儿,对于他来说就是拥有了一大笔社交晋升的财富,他张罗女儿的婚事不是关注女儿的幸福,而是掩着温情的面纱,利用女儿的婚姻达到自己的目的一一这种恬不知耻的自私,便是张爱玲眼中冷漠虚伪的亲情。
唯一的经验世界,独特的苍凉感觉
“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虱子!”(《天才梦》)这一震惊人心的生命体验正是来自张爱玲少女时代荒凉无奈的经验世界,这便是张爱玲在构建小说世界之前形成的基本心态。
所以,在张爱玲的小说世界里,她以“人世挑剔者”的目光无情地剖析着人性的丑恶。她写“软弱的人”,“不彻底的人物”,写他们“不明不白、委琐、难堪、失面子的屈服”。
这就是张爱玲看取人生的态度,“人的生存中有种种无奈……他们没有悲壮,只有苍凉”。正如她自己在《传奇》再版序中所言:“如果我常用的字是‘荒凉’,那是因为思想背景里有着这惘惘的威胁”。
一个艺术家,大约无可奈何地要忠实于自己的生活经验与感觉,他唯一能办到的,只是尽其所能,用最精妙的技巧把自己的生命世界中的一切彰现出来。张爱玲的小说,正是她曾经的生验和感觉的展现。

在一篇题为《写什么》的散文中,张爱玲明白无误地说:“文人讨论以后的写作路径,在我想来是不能想象的自由一一仿佛能有这样的选择余地似的……他写他能够写的,无所谓应当。”所以,张爱玲的小说题材选择了“世俗的圈子”,这同样也基于她进入创作以前的生活经历和体验。
“文人应该是园里的一棵树,天生在那里的,根深蒂固,越往上长,眼界越宽,看得越远,要往别处发展也未尝不可,风吹了种子,落到远方,另生一棵树,可是,那到底是艰难的事。”(《写什么》)
做为上海租界遗老家庭中长大的小姐,张爱玲的“生命世界”里摇摇晃晃的,只是来去着一批婚姻是唯一出路,而又各自莫名奇妙地被不同方式的婚姻宰制着终身命运的旧式或半旧式的庸常妇女,她的写作题材还能有什么选择的余地?
有着“古墓般清凉的”旧宅第,生活于其中的遗老与遗少,有着各种各样小心眼、小烦恼、小算计的家庭里的女人,以及生活的场景、服装的样式变换、人物的每一个眼神,每一个手势,甚至每一个细节的细微变化,都是张爱玲所熟悉的生活,有着拈手即来的灵感,她老练而真诚地扫描着他们灵魂的疲惫,对时代的恐惧,对现代文明的失望,以及人生的缺憾和千疮百孔、残缺不全的人伦感情。
这使得她的小说并不显出因悲哀、恐惧而产生的悲壮,而只是一种“古道西风瘦马,断肠人在天涯”的苍凉。
在张爱玲的小说中,已经大致完成了她对人生的基本理解,这种理解来自她生命体验最深刻的部分一一她早年的生活经历、个人遭遇。
这种生活经历和个人遭遇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是惟一的,它并不漫长,也无激烈的大悲大喜,但绝不肤浅,足以构成一个独特的,深邃的,相当完整的张爱玲精神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