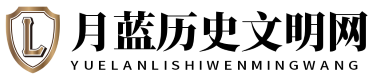女吊(4)
9、死祭 这一天,是男旦死了整整三年。 半夜,一阵冷风突然灌进东厢房,把床上睡得正香的小生吹醒了。他迷迷糊糊睁开眼,却发现身边的飞雪不见了。小生四下看看,没人,却发现窗子被吹开了,冷风直灌。小生忙起身去关窗。手刚碰到窗框,却看见一个红衣红裤的影子忽地飘了过去,小生猛地一惊,赶忙披衣出屋,可他一直走到墙角,也没看见一个人。他一路东张西望,却没注意到自己身后,一双死白的手。已缠上了他的脖子…… “谁?”小生掰住那双手,拼命挣开,转身一看,却是飞雪,小生扶着脖子喘着粗气问:“你,你干什么吗?” 飞雪笑了笑:“去看了看孩子,刚看见你在这儿逛荡,吓唬吓唬你。” “瞧你,吓死我了。”小生摸了摸脖子,抬眼不经意地看了飞雪一眼,飞雪的眸子在月光下显出些蓝色的光,脸色也格外苍白。小生看着她心里无来由地一哆嗦,转身进屋了。飞雪看着小生的背影,露出了一个更深的笑,那咧开的唇角边露出两颗尖利的牙齿,发着幽幽的光。转过身去的小生自然不知道,此时此刻。飞雪身后有一个穿着红衣红裤的影子,正伸出一双死白的手,从后面撑起了飞雪的笑容…… 两人进了屋,吹灯。小生却觉得比刚才站在外面还冷,不禁裹紧了被子,翻了个身。过了一会儿,他迷迷糊糊快要睡去的时候,突然感觉飞雪慢慢爬上了他的身,小生一惊,正要回头,却被飞雪的手牢牢压住了脑袋,动弹不得一 “你,你干什么?”小生问道。 “不干什么,就是想和你唱出戏。”飞雪低声说道,幽幽的声音夹杂着丝丝窃笑,穿进小生的耳朵,听起来却像是从很远的地方传来似的。 小生已经是一身冷汗了,飞雪的手不仅没有松开,反而越缠越紧,越变越长,海带似的,慢慢缠上了小生的脖子。而她却只是像梦游一样,在小生的耳边自顾自地低声吟唱—— “玉蝴蝶,玉扇坠,蝴蝶本应成双对……”小生的面色已经开始发自,舌头越伸越长。 “记得草桥两结拜,同窗共读有三长载……”小生的眼球渐渐凸出,似乎随时会爆裂一般。他痛苦地伸出手在空中胡乱抓着,飞雪却不躲不闪,仍是低声浅笑,自顾自地唱。 “我看你一眼闭来一眼开,问你梁兄丢不下谁?”小生的眼里已流出血来,脸上布满惊恐的神色。他已认出这声音,不是飞雪,而是从小和他一起搭台唱戏的——男旦。此时,飞雪的脸也渐渐变了模样,变成了男旦那张温和俊秀的面孔,他穿着女吊的红衣红裤,脸上涂着白粉,眼圈乌青,看着七窍流血的小生,他开心地笑了,露出两颗尖而亮的牙,慢慢地,狠狠地咬住了小生的喉咙…… 第二天,戏班子的人惊恐地发现,东厢房里横着两具尸体——一具是穿着浙丝睡衣的飞雪,表情惊恐,身上没有半点伤痕。更离奇的是,她身边还躺着另一具尸体,居然是死了三年的男旦!戏班子赶紧差人报了官,仵作也验不出个子丑寅卯来,最关键的是——小生失踪了。 扬州城里炸了锅,有人说,这是鬼魂作祟,冤死鬼回来找债主了,可小生哪儿去了?也有人说,是这小生贪图飞雪的钱财,于是杀了她然后掘出了男旦的尸首,让人以为是鬼魂作祟,可死了三年的人怎么还没烂?各种说法都不靠谱,衙门也糊涂了,弄了张通缉小生的告示贴出去,日子一久,小生没抓到,告示也烂了。兵荒马乱的年月,谁也管不了谁。 10、谁都逃不掉 戏班子选出了新班主,日子还得过下去。这一天,戏班子里很忙碌,第二天他们要去城里的孙大老板家唱戏。孙老板财大气粗,要为他去世三年的母亲办堂会,指名道姓地点了《跳吊》。就在大家忙得脚不点地的时候,突然来了个衣衫破烂的道士。 “这道士我认识,吴班主他们夫妻俩还在的时候,他好像来过。”唱老生的老何小声告诉新班主。是的,这个脸上有道疤的道士来过,来的时候班里也正是在唱《跳吊》。新班主想到这里,赶忙领着道士进了里屋。 “贵班明日可是要唱《跳吊》?”道士倒是开门见山。 “是。”新班主很平静地回答道。 道士笑了笑说:“不怕吗?” 新班主盯着道士,手心里渗出一层汗来:“啪?怕什么?” “恶有恶报,老天长着眼睛呢。”道士波澜不惊地说着,这话却像重锤般狠狠地击打着新班主的神经。 “你……你什么意思?”“那男旦死的时候怨气重,必然不肯轻易转世投胎,所以专门请了定魂石压在他的坟头,好让他的魂魄无法出来作乱。 可是—是谁搬开了他坟头的镇魂石,让他出来害人的?”道士死死地盯着新班主。新班主头上已冒出汗珠,“你——你是谁?” 道士仍然只是笑:“我不过是个臭道士罢了,只是碰巧听说了你们的事,当年在男旦坟头放定魂石,也是我教给吴班主的。” 新班主结结巴巴地追问道:“你……你还知道什么?” “我还知道——”道士不紧不慢地说道,“有的人,见钱眼开,偷偷挪开了定魂石,放出了男旦的怨魂。”道士挥了挥拂尘,问道,“你难道就不怕班主夫妇的怨魂回来找你么?” “怕?我怕什么?”新班主猛地站起来,“那对奸夫淫妇又是什么好东西?我们戏班子搭台唱了这么多年,无功劳也有苦劳!她一个窑姐凭什么爬到我们头上作威作福,还有那个没种的男人,为了个不要脸的女人,连兄弟都不要了,这对狗男女死一千回也不嫌多!”新班主愤愤地说。 11、尾声 “死人了!”台下不知是谁喊了一声,大家轰地四下散开,夺门而逃。混乱的人群里,有一个女人却很平静,静静地在角落里站着,看着眼前的一切,空空的眼眸里映出吴府大院里的一片狼藉——她是小红,或许我们该叫她飞雪了吧,毕竟讨到了替代的飞雪,仍旧是飞雪。没什么可惊讶的,做人能干的女人,做了鬼也一样能干。还记得十六年前扬州城戏班子的那出跳吊惨剧吗?难道你们忘了,男旦在事发当夜就带着小生的儿女远走他乡了,那么两个月后,男吊在悬布的照妖镜里看到的吊死鬼,又是谁呢? 从那天起,飞雪就讨了那日唱女吊的小红当自己的替代。飞雪是个豌豆一样的女人,只要能活着,她就会削尖脑袋活下去。哪怕活不成,她也不会甘心当个屈死鬼。然而女人总归是女人,再刚强也逃不过“情”字。所以飞雪仍然愿意守在这个怨鬼组成的戏班子里,守在小生身边,并且费尽心机一路指引他们来了乌桐镇——她要亲眼看到男旦死在小生面前,她要亲眼看到小生在她面前给一个取舍,给一个交代。现在她如愿了,可是她没想到小生也一剑穿心,将自己和男旦牢牢地钉在一起。 “罢了,愿赌服输。”飞雪苦笑一声,仰头将泪水生生咽回去,她看了看和小生蜷缩在一起的男旦,“你取了我的命,占了我的男人:我做的孽,你来替我承担,我们两清了。”飞雪转过头,缓缓向吴府大门走去。 吴府大院被封了,吴家少爷和小姐搬了家。吴祥仍然尽心尽力地伺候左右,因为自己的良心债——米铺被盗的事儿是吴祥的侄儿所为,为了逃脱干系,他侄儿又装神弄鬼往米里撤了鸡血。吴祥事后虽然把他赶出了米铺,但他却怕牵连自己。隐瞒了这事。于是,他听说谢班主要“捉鬼”的时候,像抓到了救命稻草,又害怕又兴奋。 只是吴祥没想到,这样一出戏,差点把整个乌桐镇的人都给唱没了。那天半夜小红的回眸一笑,吴祥不知道小红是否知道他做过什么,但那微笑,让他一辈子再也不敢做亏良心的事儿,随其缘对,,谁都别自作聪明。这个故事到此为止就结束了,文爷没有告诉我们飞雪后来去了哪里。 或许,她游荡在自己的儿女身边,默默地守着他们吧。吴府的大门上贴着一张驱邪桃符。说是要封住冤魂。可每年四月初七,大院里都会隐隐传来唱戏声,起初大家都害怕,不过听久了,只觉得好听,也不怕了。 桃木穿胸的男旦和小生是一起下葬的,坟头上竖了两块石碑,石碑上写的名分是——兄弟。——立坟牌,梁兄你红黑两字刻两块。黑的刻着梁山伯,红的刻着祝英台。我和你生前不能夫妻配,我就是死也要与你同坟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