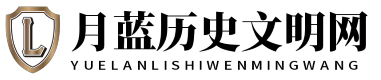翟玉忠法家与合作主义
中国人用自然主义的整体观看待国家体系时,他们很容易摆脱机械论的影响,这使得中国人在哲学方法上具有独特的优势地位。

(作者:翟玉忠,国学专家,财经评论家)
上个世纪初陈启天先生(1893-1984年)研究法家的时候,就注意到了法家与国家主义的联系,认为儒家的基本立场是宗族主义,墨家的基本立场是世界主义,道家的基本立场是个人主义,而法家的基本立场则是国家主义。这里的“国家主义”实际上主要指当时流行的合作主义。
为什么中国古典经济学与欧洲合作主义的哲学有相似点呢?关键在于,二者都认为国家不是个人的简单加和,而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国家有机说是合作主义的主要思想源头之一。
中国人用自然主义的整体观看待国家体系时,他们很容易摆脱机械论的影响,这使得中国人在哲学方法上具有独特的优势地位。
西方国家有机说的代表人物是德国哲学家费希特(J.G. Fichte,1762一1814年)和黑格尔(G.w. F. Hege1, 1770一1831年)。黑格尔认为国家不是被动的机械,而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国家有自己的意志,国家是伦理理念的现实——作为显示出来的、自知的实体性意志的伦理精神。黑格尔用他极富思辨的语言论证说,离开了国家整体,不存在抽象的个人,国家的普遍利益高于个人利益,他认为,“国家是绝对自在自为的理性的东西,因为它是实体性意志的现实,它在被提升到普遍性的特殊的自我意识中具有这种现实性。这个实体性的统一是绝对的不受推动的自身目的,在这个自身目的中自由达到它的最高权利,正如这个最终目的对单个人具有最高权利一样,成为国家成员是单个人的最高义务。” (黑格尔:《法哲学原理》,商务印书馆,1996 年, 第253页。)
黑格尔的这种思想完整地被意大利法西斯家继承了下来,他们认为只有不同阶级平衡地统一于有机的国家中,实行阶级合作,国家才能强大。这里国家超越了阶级的界线。墨索里尼强调:“不论怎样,公有秩序是不能扰乱的。意大利需要经济上的和平,以求资源之开发。工团主义者和资本主义者必须明了新的历史事实;他们要避免事态的决裂和阶级斗争,因为阶级斗争足以破坏国家。政府不受任何团体的指挥,而是站在一切团体之上,不仅代表目前国家的意识,而且代表将来国家之一切构成份子。”(转引自吴友三,《法西斯运动问题》,商务印书馆,1936年。第110-111页。)
站在历史更高的纬度上,我们已经能够将国家有机说建筑在科学的哲学——系统哲学基础之上——可以毫不夸张的说,系统哲学是亚里士多德时代以来人类知识领域的最伟大。
现代哲学命运的转折点发生在20世纪中后期,随着信息论,控制论,非平衡态热力学,协同学等学科的出现,系统哲学在科学的沃土上获得了新生。人类开始从研究实体转向研究关系,从研究局部转为研究整体,从纵向深入研究转向学科横向研究,科学开始了伟大的回归——回归它的母体——哲学,通过“科学的哲学化”哲学获得了更坚实的基础。
除了系统论所带来的本体论、认识论、价值论以及崭新的非线性发展观,系统论的伟大贡献之一在于它重新确定了国家的性质。国家是在生态系统和社会系统上进化出来的以人为基础元素的开放自组织系统。它按照系统的普遍逻辑发展,像所有远离平衡状态的自组织结构一样,国家具有等级结构,等级控制和自主调节的特点。
在系统论那里,中国古典经济理论和合作主义似乎重新“发现”了自我。今天,我们能够用科学理论证明机械论以及建立在机械论之上的诸多西方经济理论的偏狭。系统论发展中的里程碑式人物,奥地利理论生物学家路德维希•冯•贝塔朗菲(Ludeig von Bertalanffy)在其1955年出版的专著《一般系统论》中就曾指出,机械论的观点是错误的,有机体不是机器,不能被分解为诸要素,并采用简单地相加来说明有机体的属性;有机体也不是在只有受到刺激时才能反应,否则就静止不动。
当把贝塔朗菲的系统理论应用到国家这个巨系统的时候我们不难发现:国家不是像原子那样堆积起来的简单集合体,国家有自己的控制中心,有自己的意志和能动性,这些意志栖息于家、艺术家、哲学家、军人、商业领袖、及每位国民的心中,并通过法律、伦理、教育等形式具体化。国民也不是无区别的原子,他们是与国家有机地联系在一起的。
系统论是思想的利剑,它告诉我们现在和过去人们已经习以为常的某些观念是怎样的无知和愚蠢。尽管那些观念听起来冠冕堂皇,但它们总是将人类沉入冰冷的现实之中,甚至会将之带入灾难的境地。哲学是人类社会变革的先声与号角,它是人类精神遗传信息的突变和国家系统中社会文化信息库的更新。在此意义之上——让哲学女神成为世界之王吧!
合作主义的另外两个主要思想源头是天主教关于现代经济社会问题的观点和职团主义。
谈到天主教关于现代经济社会的观点,我们不得不提及美因茨主教冯•凯特尔男爵(Baron von Ketteler ,1811~1877年),正是在这位德国贵族的影响下教皇利奥十三世(Leo XIII 1810~1903)于1891年5月15日发布了《新事物》(Rerum novarum)通谕。《新事物》通谕也称《劳工通谕》,这份意义深远的天主教官方文件既谴责了资本主义社会少数人对多数人财产的剥夺和它对财富的乱用,又批评了,认为它违背了人类固有的财产权力。一方面同情广大劳工阶层的贫困,劝诫富人阶层和国家关怀各个阶层的共同福利;另一方面反对废除私有制,反对暴力,认为这将危害劳工自身。《新事物》主张资方和劳方真诚合作、互补不足,并提议工人天主成立天主教工人联合会。
冯•凯特尔男爵在他那本著名的《教与劳工问题》(Die Arbeiterfrage und das Christenthum )一书中明确指出:资本的无上地位和经济自由主义是现代社会两大罪恶之源,二者代表着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的胜利,它们将瓦解使人成为有机道德人的所有力量。工人阶级先是被分化为原子状态,然后被机械的组装起来;为了现代社会将工人“原子化”的企图,冯•凯特尔男爵建议成立包括一个职业所有成员组成的行会。
在建立职业工会这一点上,职团主义和冯•凯特尔男爵有相似的地方——正是职团主义者第一次赋予了工会国家职能。二者关键不同在于早期职团主义者是赞成阶级斗争的,而法西斯的职团是有机国家的内在组成部分。墨索里尼时代家,法学家罗谷(Alfredo Rocco,1875-1935年)认真区分了二者的不同:“旧时的职业团体是产生于国家之外,存在于国家之外,而我们的职业团体却和他们不同。我们的职业团体,是国家的一部份,是国家的力量和威势的因素。而这个国家的职业和合作组织给予意大利社会一个新的结构。这个结构,不再以法国哲学中所含的个人原子论为基础,而是根据于一个真正有机的国家观。”(转引自吴友三:《法西斯运动问题》,商务印书馆,1936年。第90页。)
职团主义最早诞生于十九世纪末期的法国,代表人物有拉卡德(Hubert Lagardelle 1875~1958)和索列尔(G. Sorel,1847-1922)。之后职团主义在意大利、西版牙,以及北欧、中南美洲一些国家广泛传播。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著名意大利职团主义者如兰兹洛(Agostino Lanzillo )和比昂基( Michele Bianchi)等在意大利职团国家建立过程中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人学研究网·中华文明栏目编辑:紫天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