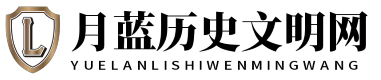南方丝绸之路的历史价值
南方丝绸之路开通以来内接中原,外联南亚、东南亚,是佛教南传、藏传,本土宗教的交汇地,独特的地理位置,杂居交错的民族聚落,构成了独特的地域文化,是中原文化、藏传文化、东南亚文化及当地民族文化融合的产物。从文化线路上来说,这些区域就是费孝通先生所定义的“藏彝走廊”地带,也是“三圈说”的“中间圈”区域。

南方丝绸之路沿线处于中央版图边缘地带,一方面跨境而居,与当地土著在物品上互通有无,语言上交流通畅;一方面受到中央王朝管控,遥远的王权管控远达于此,在政令上畅通有效,儒学传统文化远播于此,通过人员交流、物品交换,在上下一体的秩序中,核心、中间、海外三圈间文化出现了上下纵横勾连。
处于“中间圈”地带上少数民族是主体,但长期与汉族杂居交融,贸易的终点又延伸至“核心圈”“海外圈”范围内,构成了“边缘”与“中心”的互动。
南方丝绸之路是多国、多地域、多民族文化的碰撞和融和、排斥和吸收,是混合体而不是单一民族的特产。它对外来文化既没有照搬、移植或简单的改头换面,而是本土文化与多种外来文化碰撞融合,和谐共生,和而不同的复合文化。转运于不同时空中的丝绸、茶马,一路适应、融合,最后移植生根,在不断地适应中变迁,不断的创造再生,将圈内圈外的文化勾连融合,浑然一体。
考古学证据表明,中国古代文明经由西南地区与近东文明之间的接触和交流,在公元前第二个千年的中叶就已存在了,其间文化因素的交流往还,多经由南方丝绸之路进行。四川和云南考古发现的来自西亚的石髓珠和琉璃珠,都证明中国西南与西亚地区的经济贸易和文化关系早已发生的事实。
商代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青铜雕像群和金杖、金面罩,由于上源既不在巴蜀本土,也不在中国其他地区,但却同美索不达米亚、埃及、印度等世界古代文明类似文化形式的发展方向符合,风格一致,功能相同,在年代序列上也处于比较晚的位置,因而就有可能是吸收了上述西方文明区域的有关文化因素进行再创作而制成。
西方考古发现,希腊雅典kerameikos一处公元前5世纪的公墓里发现了5种不同的中国平纹丝织品,织法与四川丝绸相同。埃及和欧洲考古发现的中国丝绸,与中国考古发现的印度和近东文明的因素,两者在中西文明交流与互动的发生、发展年代上吻合。
西方地中海地区的古希腊、罗马,最早知道的中国丝绸,便是来自古蜀地的产品。由此可知,从中国西南到印度,再从印度经巴基斯坦至中亚阿富汗,由此再西去和西亚、欧洲地中海地区和北非埃及,这条路线正是中国丝绸经由南方丝绸之路西传的交通线。
古代巴蜀丝绸在世界各地的传播,丰富了印度、中亚、西亚、北亚和欧洲文明的内容,而这条因丝绸传播而形成的线路,不仅对中国早期西南地区的经贸繁荣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对南亚、东南亚、中亚等地的经贸繁荣也有较大的影响。
不仅如此,南方丝绸之路对于中国西南地区以及东南亚、南亚的民族融合起到了重要作用。考古材料显示,自夏、商时羌系民族便经青藏高原的东缘(四川西部)向西南地区迁移,此后这种民族大迁移络绎不绝,到战国时期“因畏秦之威”又一次达到。这些迁移的民族不单到达西南夷地区,一部分甚至进入了东南亚及南亚的东部地区。民族的迁移打通了沟通南北的交通通道,促进了文化交融。
南方丝绸之路在历史意义和价值意义上是世界性的,它具备的文化个性和创造精神不可替代。这种创造性是南方丝绸之路开放精神的必然产物,沿线文化是南方丝绸之路沿线族群的民族文化精粹的集中表现,是该线路民族文化的标志,是整体性的象征。
南方丝绸之路文化在漫长的发展史上,已渐渐转型为象征精神,马帮终将消失,但这并不意味着文化的彻底消逝,沿线旅游、博物馆,茶叶交易新市场等,无不是以茶马文化为内核的发展开拓,而这些也必将随着“一带一路”战略实施继续传承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