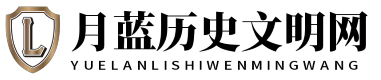离散译者张爱玲的中英翻译
“作家张爱玲”众人皆知,但”译者张爱玲”知者相对较少。
其实,名闻遐迩的”张爱玲”名字本身就是翻译而来的。张爱玲小名张煐,英文名Eileen Chang,十岁临入学时,母亲情急之下才把Eileen Chang翻译成中文”张爱玲”。

读者及译界权威人士都认为张爱玲对美国文学的翻译是非常优秀的,无论与当时甚至现在一般的中文译作相比较,张爱玲的译文都称得上是佳译。张爱玲的部分作品甚至是先以英文创作,再重新改写成中文的。
然而,在国内对现代美国文学的译介中,张爱玲的译者身份和成就始终处于近乎空白的位置。
翻译作品
张爱玲于1952年离开新中国,到了香港,受雇于美国新闻处驻香港办事处(简称:香港美新处)做翻译。在上个世纪50-60年代期间,张爱玲翻译了大量美国文学作品,类型则广涵小说、诗歌、散文、戏剧与文学评论,以小说居多。
其中有海明威的的《老人与海》(1954年11月出版),还有:爱默生的《爱默生选集》(1953年出版),玛乔丽·劳林斯的长篇小说《小鹿》(1953年出版),欧文的《睡谷故事》(1955年出版),《美国诗选》(合译,1961年出版,张爱玲负责其中爱默生和梭罗部分)。
翻译自己的作品:《秧歌》(The Rice-Sprout Song)与《赤地之恋》(Naked Earth)均分别以中英文撰写与出版,英译自己的小说《等》(Little Finger Up)、《桂花蒸阿小悲秋》(Shame,Amah!)、《金锁记》(The Golden Cangue)。
译注清朝吴语方言小说《海上花列传》(中国第一部方言小说)为国语《海上花开:国语海上花列传一》和《海上花落:国语海上花列传二》,并翻译为英文《The Sing-song Girls of Shanghai》。
作为一位杰出的翻译家,张爱玲的翻译原则主要是以目的语读者为导向,译文致力于符合目的语读者的语言习惯,同时准确传达原文的含义。

多种策略并用
纵观张爱玲的翻译,可发现其翻译往往是根据读者需要多种手法并用。如她将《海上花》不少部分删去不译,她在注释中解释这是为了满足西方读者需要:“Perhaps understandably concerned about its reception abroad,I finally took the liberty of cutting the opening page...”。
而在翻译《桂花蒸,阿小悲秋》时,原作约3588字并未翻译,她将故事中关于西方人的负面描写省去以免引起读者不快。增译在张爱玲的翻译中也是频频出现。如在翻译《桂花蒸,阿小悲秋》时,为了便于读者理解,张爱玲增加大量说明介绍阿小的丈夫。
尤其是在涉及文化差异时,她往往在译文中添加说明。改译也是张爱玲惯用的翻译手法。如译《海上花》时,她将人名“赵朴斋”译成“Simplicity Chow”,“洪善卿”为“Benevolence Hung”以便西方读者能记住这些人物,理解人物性格。
忠实于原文
尽管有时张爱玲的翻译与原文有异,但不能说这与忠实性有违。
夏志清在Twentieth Century Chinese Stories里评论张爱玲:“edited all the translations with great care to ensure their readability and fidelity to the original’”。为了忠实于原文用人名体现人物特征,张把“阿招”译成“Beckon”,“阿巧”译成“Clever”。
在翻译《金锁记》时,她直译“窗外……白的太阳”为“Outside the windows there was still that abnormal moon that made all ones’body hairs stand on end-small white sun brilliant in the black sky”。她保留了长长的修饰语,而这在英语里是少见的。
这样的直译造成了西方读者的陌生感与怪异感,从而营造出与原文相似的气氛。
与形式上的忠实比较,张爱玲更重视的是意义上的忠实。

当文化差异过大以至于一味追求形式上的一致可能会造成读者理解上的困难时,她通常会放弃形式上的一致。如她将“藕断丝连”译成“persist in a friendship with their daughter after the break”,“将计就计”译成“managing the best she could”.这在选词造句上与原文有异,但却直接表达了原意,达到原文预期的效果。
要正确评价张爱玲,在研究其文学创作的同时关注其翻译是有必要的。研究发现张爱玲的翻译原则主要以目的语读者为导向,多种手法互为补充,其译作既忠实于原作,又易于被读者接受,译笔优美流畅,丰富了中国翻译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