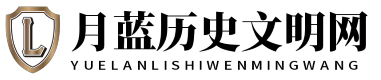论唐朝传奇中侠客形象的演变
20世纪下半叶至今,武侠题材小说的创作极度繁荣,蔚为大观。如果考察它在小说史上的源流,则必定追溯到唐传奇。唐人“始有意为小说”,“文采与意想”皆有可观[1],被誉为中国小说史上第一座高峰,而“豪侠”正是唐传奇三大表现题材之一①。中晚唐时期士人对豪侠题材产生浓厚兴趣,塑造了一大批各具风姿的豪侠形象,留下不少传世佳作,并对后世的武侠文学产生深远的影响。唐传奇中的豪侠其实有它的历史渊源,并非全凭空想捏造而来。不过同历史上的游侠相比,唐传奇中豪侠的内涵性质和行为特征都在发生变化,作家根据自己所处的历史背景和生活感受不断调整“侠”的观念,把他们对“侠”的理解通过笔下不同的形象表达出来。通过对唐传奇的豪侠群体作类型分析,能够发现这个观念变化的核心线索是“武”与“侠”的合流与分异,从这个层面看,唐代豪侠小说正处于一个承上启下的位置,正是“武”、“侠”内涵的分合变化为后世武侠文学创作的多样化可能性打开了一片新天地。

一、唐代以前“侠”与“武”的观念和侠客形象之滥觞
人们习惯“武侠”联称,但其实各自涵义不同。“武”是武功,是技击本领,是工具和手段;侠是一种精神特质,是一种行为姿态,具有这种精神、以这样的姿态行动的人亦称为“侠”或侠客。“侠”的概念最早出现在韩非子的《五蠹》中,他认为侠是“带剑者”,他们“聚徒属、立节操以显其名,而犯五官之禁”,虽然剑作为武器已伴随侠客初露端倪,但无论是韩非、司马迁还是班固都并不注意这个,他们着眼的是侠“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己诺必诚”、“振穷周急”的精神,为“赴士之困厄”不惜“时扦当世之文罔”[2],或者如班固反面评价的“以匹夫之细,窃杀生之权”[3]的自掌正义的姿态。《史记》、《汉书》为游侠立传,无论是卿相之侠如孟尝君、春申君、平原君、信陵君,还是布衣之侠如朱家、郭解、剧孟等,均未见有何过人创武功。最著名的侠客荆轲刺秦的场面绝非如电影《英雄》中那般眩目,不过是普通人之间的搏斗:“左手把秦王之袖,而右手持匕首椹之”,“荆轲逐秦王,秦王环柱而走”,秦王拔剑以击荆轲,“断其左股”[4],而事遂不就。故陶渊明叹日“惜哉剑术疏,奇功遂不成。”没有武功却被推崇为侠客中最上品的“神勇之人”,只是因为荆轲具有舍生取义、无所畏惧的胆气和精神。不过《吴越春秋·勾践阴谋外传》中,有对精深剑术的祥细描述。白猿与越女比试剑术,越女的剑术神妙莫测。越王问其击剑之道,越女日:“其道甚微而易,其意甚幽而深。道有门户,亦有阴阳。开门闭户,阴衰阳兴。凡手战之道,内实精神,外示安仪,见之似好妇,夺之似惧虎,布形候气,与神俱往,杳之若日,偏如滕兔,追形逐影,光若佛仿,呼吸往来,不及法禁,纵横逆顺,直复不闻。斯道者,一人当百,百人当万。”[5]这是一段非常精彩的剑术练论,说出了最上乘武学的道理,无怪越王赞道“当世莫胜越女之剑”。越女是精通剑术的武术高手,但没有任何侠义事迹,显然不是一个侠客。综上所述,可知先秦两汉时代,“侠”并不与“武”有何密切联系,两个概念之间没有必然的交叉。不过从小说史的角度看,《史记》、《汉书》中的游侠群体和《吴越春秋》的越女形象分别阐释了“侠”与“武”的内涵,成为后世豪侠小说之滥觞,在“武”“侠”内涵的交织变异过程中,孕育出大批风姿各异的豪侠形象。
二、从唐传奇中豪侠的类型特征看“武”、“侠”观念的合流与分异
不同时期的唐传奇中豪侠形象有不同的特点。中唐时期的《谢小娥传》、《柳氏传》、《柳毅传》、《冯燕传》等小说刻画了一批轻生死、重然诺、爱惜名节、鄙弃财禄的豪侠义士形象。他们虽然举止各异,社会身份也互不相同,然而都具有一种气势浑厚的道德风范和纵横捭阖的人生情态。谢小娥身为女流,“呼号邻人并至”才活捉申春,并不比一般人有力量;黄衫客为霍小玉打抱不平,不过是“挽挟其(李益)马,牵引而行”;柳毅只是一介儒生,即如许俊(《柳氏传》)、冯燕(《冯燕传》)、古押衙(《无双传》)、郭元振(《郭元振》),也都是没有神奇本领的常人,他们为人排忧解难,靠的不是武功,而是胆气、精神。追溯源流,中唐时期小说中的豪侠接近于《史记》《汉书》所记的“布衣之侠”、“闾巷之侠”。
晚唐豪侠小说与中唐又有所不同,在侠义精神之外,作者着重强调了侠客身怀高深的武功、能使神秘的道术。小说中侠客多用剑,又多有女性,如红线、聂隐娘、贾人妻、车中女子等等,这与《吴越春秋·勾践阴谋外传》中越女的故事一脉相承。越女剑法一人当百,百人当万,其中还蕴涵着道的玄机。而京西店老人、兰陵老人(皆出于《酉阳杂俎》)、聂隐娘(《传奇》)的剑术同样深不可测。兰陵老人“拥剑长短七口,舞于中庭。迭跃挥霍,〓光电激。或横若掣帛,旋若规火”,剑气使黎干心胆俱丧,且兰陵老人又善谈养生之道,而昆仑奴磨勒10年之后尚容颜如旧,卖药于都市。剑术之外,崔慎思妾、车中女子(皆出于《原化记》)都能飞檐走壁、轻捷如鸟,这似乎是对“轻功”的最早想象。聂隐娘不但武功高强,而且能变幻身形、善隐身之术,此外还能化尸为水,剪纸成物。红线(《甘泽谣》)在额上书太乙神名,就能“夜漏三时,往返七百里”,从田承嗣枕边盗走金盒。这些侠的行迹已近乎仙,非常人常情所能揣度。中唐小说中的豪侠与世人生活在同一个世界,而此时精深神秘的武功已经将侠与世人分离。从小说本身来看,无论是展开情节还是塑造形象,“武”的因素已经必不可缺。在另一些更晚的豪侠传奇中,“武”成了作者关注的唯一要素。《剧谈录·潘将军》中,潘将军有一串宝玉念珠,“储之以绣囊玉合,置道场内,每月朔则出而拜之。一旦开合启囊,已亡珠矣,然而缄封若旧。”原来是一“三鬟女子”为了与“朋侪为戏”而窃,游戏过后即完璧归赵。《田膨郎》(《剧谈录》)情节与此相似,唐文宗所珍视的白玉枕被田膨郎从“寝殿帐中”偷走,而这个“行止不恒,勇力过人,且善超越”的田膨郎又为王敬弘小仆。作者为小仆安排了飘然归蜀,如鹤远翔的结局;又借皇帝之口评论田膨郎道:“此乃任侠之流,非常之窃盗也。”在这里作者亦表达了对侠的敬意和羡慕,但只见此“侠”之“武”而未见其义,已全非中唐之“侠”。
回顾侠客形象变化的过程可见:中唐小说中的豪侠是普通人中的一员,其独特在于不屈的精神、无畏的胆识,他并没有高深的武功,在道德方面却堪为人表率,强调的是侠之义。晚唐小说中人物行侠开始要倚仗神奇莫测的武功,“侠”与“武”开始结合,“以武行侠”的观念大致定型。随着时代的变迁,小说中的侠最终变成了仙或者近于妖:他容颜不老、性情冷峻、超然于儒家的伦理纲常之外。不必有“义”,只要有神妙的武功和道术就可称侠,强调的是侠之武。经历一个“武”和“侠”的观念合流与分异的过程,由中唐到晚唐,侠客的面貌已经变化得截然不同。
三、观念变化的深层原因
同诗歌对侠客的歌咏一样,士人作豪侠传奇亦是有感于时世,寄托了某种情怀的。时代和自身生存处境的变迁影响到士人的创作心态,作家于是根据自己所处的历史背景和生活感受不断调整“侠”的观念,通过笔下的形象表达对“侠”的不同理解。从这个层面看,“武”“侠”观念的分合变异是时代背景和士人这个特殊社会阶层自身文化生活方式、思维方式、价值取向等方面发生的一系列变化而导致的。
唐代科举制度的建立和完善使更多的寒士能够进入统治集团,“仕”在士人生活中的地位和价值不断提高,而与此同时,士阶层的传统地位则逐渐跌落,不再可能实现“上为王师,下为伯友”的理想。在科举制度下,皇权通过公开的考试招募需要的人材,被招募的人材臣服于皇权,士与“势”的关系颠倒过来,皇权和统治者成了“师”,而应举的士人则成了“学生”。唐太宗当年站在端门上,看到“新进士缀行而出”,说“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6]。而德宗试制科于宣政殿并亲自阅卷,翌日,则遍示宰臣、学士日:“此皆朕门生也!”[7]这说明科举制度发展到中唐,士人完全失去了与势力抗衡的能力,沦为了政权的附属物。士人要想实现自己的抱负就必须依托和屈从于皇权和统治者,为之所“用”,久而久之,这种特殊的社会地位使士人普遍地养成了一种依附性格。此外干谒(唐人科举的题中应有之义)又往往使士人饱尝失去个体人格尊严的痛苦,杜甫晚年回忆起干谒生活仍然十分酸楚:“长安秋雨十日泥,我曹鞴马听晨鸡,公卿朱门未开锁,我曹已到肩相齐!”[8]士人一向注重内心修养,自爱自重,然而要入仕就得屈己干人,枉道从势,这是一个两难的选择。士人深知自己依人成事和不能平视王侯而需以俳谐求容的人格缺陷,却又无从超脱,内心不能不感到失衡和压抑。对比自身的优柔寡断、患得患失,士人转而倾慕侠客义士的从心所欲,放任不羁。
柳毅在钱塘君逼婚时,“肃然而作,软然而笑”,“敢以不伏之心,胜王不道之气”。因为不想为官作宦、贪名竞利,对权势者无所求,因而在精神上与之完全平等,无须逆来顺受,委曲求全。谢小娥为亲人复仇,尽管艰难,终于达到了目的,不是依人成事,而全凭一己之力。可以说这些正是士人依附性格和娼优气相的对立面反射,而冯燕“己为不平能割爱,更将身命救深冤”的敢作敢当,许俊突袭沙吒利劫出柳氏的英勇果断,与书生的懦弱无用、迂腐怕事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侠客独立不羁的个性、豪迈跌宕的和如火如荼、飞扬燃烧的生命情调令人如此神往心驰,可以说小说的作者正是要以侠气来反照自身、激励同侪。
晚唐则不同。晚唐是一个乱世,宦官、藩镇和党争的老问题无法解决,农民起义又频频发生,士人失去了建功立业、杀敌报国的热情,失去了冲出绝境,重整旗鼓的勇气,同时丧失了对自己的信心。悉尼·胡克在论及公众对英雄伟人感兴趣的心里根源时,列举了几个主要原因,其一是在时代过于混乱,秩序没有建立时,出于心理安全的需要;其二是个人愿望无法得到实现,只能靠心理补偿[9]。司马迁亦云:“且缓急,人之所时有也”,“况以中材而涉乱世之末流乎?”[10]叫书生身处乱世,而手无缚鸡之力,遇害尚且不能自救,于是把目光转向有神奇武功的侠客,希望他们能“救人于厄,振人不赡”。《昆仑奴》中红绡妓被朝廷一品勋臣倚仗势力逼为姬仆,昆仑奴仗义行侠,将她救出牢笼,“负生与姬飞出峻垣十余重”,成就了一段美满姻缘。《红线》中红线深夜潜入魏博节帅的寝所,以行刺相威胁,迫使田承嗣收敛吞并潞州的野心,虽然只是一个青衣,却拯救万民于水火,解决了朝廷也无能为力的问题。《床下义士》记一县宰遣刺客谋害昔日的恩人,刺客知道事情的原委后就杀了恩将仇报的县宰,替人报仇雪冤。正如张潮所说:“胸中有小不平,可以酒消之;世间大不平,非剑不能消之。”[11]“侠客不怕死,只怕事不成”[12],以一己之力对付社会黑暗,拯世济民,没有高超的本领恐怕难以遂愿,“武”是实现“侠”的目的的必要手段。随着国家不可挽回的走向没落,在那个制度不立,纲纪废驰的年代,唐末相当一部分士人的心态是:既然世道已无规范可言,功烈忠孝没有用处,那就随心所欲,游戏人生。这一时期小说中的侠客形象反映了人们对“以武犯禁”,“不轨于正义”的新的理解。“侠”的内涵中,正义、道德的意义已被消解,“武”不再只是手段,它变成了“侠”的全部。
丹纳曾经说过:“如果一部文学作品内容丰富,并且人们知道如何解释它,那么我们在作品中找到的会是一种人的心理,时常就是一个时代的心理,有时更是一个种族的心理。”[13]而通过对唐代不同时期小说中豪侠形象的比较分析,我们可以发现中晚唐士人精神蜕变的轨迹。大量创作豪侠题材的小说,对侠客表达倾慕之情,一方面表达了士人们对自由独立人格的渴望,这正是基于对生命价值、人性和个性的肯定和张扬;另一方面从小说中“侠”的内涵不断变窄,最后以“武”代“侠”的现象揭示了时世变迁中士人的无力感。
出于士人之手的文言的豪侠小说在中晚唐时期达到艺术成就的顶峰,更为后世各种体裁的武侠文学的创作提供了楷模。值得注意的并不是内容上的借鉴沿袭,而是蕴涵于唐代豪侠传奇中的“武”、“侠”观念的转变为后世武侠小说创作提供了广阔的视野。对“武”的想象是愈来愈丰富和奇妙,而不同时代背景下对“侠”的界定不同,“侠”的内涵中武功与道义的比例也发生了变化,侠客形象的塑造因此有了多样可能性,武侠文学的创作也更加丰富多彩。宋代小说中的侠客形象已不同于唐代,而清代小说中的侠客与唐代相比,更发生了性质的改变。
《三侠五义》、《施公案》中塑造了一群武功高强的侠客形象,如展昭、白玉堂和黄天霸等,他们行侠的主要事迹是保护一位清官,帮他锄奸灭害。正如鲁迅所说:“凡此流著作,虽意在叙勇侠之士,村市,安良除暴,为国立功,而必以一名臣大吏为中枢,以总领一切豪俊……”[14]侠客们不再以武犯禁、自掌正义、特立独行,反而以武助禁,成了法律的保卫者,而“为国立功”的企图可谓自觉地将己打碎的锁链重新套上脖子。这表明从中古到近古,随着封建政权的加强,士人们开始接受自己依附者的身份和地位,反抗的精神逐渐萎缩,心态向接受和自觉维护既定的秩序和法律转变,这是游侠形象改变的内在原因,也正是通过小说中“武”、“侠”内涵的变化体现出来的。
综上所述,正如陈平原所说:“‘侠’的观念(武侠小说中)是一种历史记载与文学想象的融合,社会规定与心理需求的融合,以及当代视界与文类特征的融合。”[15]各个时代的作家根据自己所处的历史背景和生活感受来调整“侠”的观念,塑造侠客形象,表达自己对“侠”的理解。从唐传奇来看,“侠”与“武”内涵的分合变异决定和伴随着豪侠形象演变的过程,而在这些现象背后我们也窥见了唐代豪侠小说作者和他们所代表的一个群体在特定时期的特定心态和精神风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