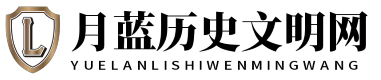李泽厚由巫到礼
易经本卜筮之书,却蕴涵、讲说着好些历史史实和经验故事,功能又仍在使人去影响客体、作用对象,主观选择性、能动性甚强,并不同于匍伏、祈祷、自甘受制于对象的宗教崇拜。

(作者:李泽厚,哲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巴黎国际哲学院院士)
我今天讲的题目是《由巫到礼》,这是个很难讲的题目,因为牵涉到上古史,材料不够,我自己研究得很不够,学术界好像也研究得不够。这是个非常重要、却被忽略掉的问题。所以的确值得讲一讲。特别是这个问题与中国整个文化、中国整个哲学的特征,很有关系,这就成了一个大问题。
怎么说呢?中国文化、哲学的特征,有什么特征呢?当然有很多了。例如,比较其他文化来说,在中国文化里,人的地位就很高。天地人三才,人可以跟天地并列,可以“参天地、赞化育”。人能够参与天的运作。我记得八十年代一个反传统的学者说,中国文化的最大的缺点、最大的问题,就是人的地位太高了,所以必须把教引进来,人必须要在上帝面前悔罪,认识自己有原罪,不要把自己地位估计那么高。《圣经》里没说人能够参与上帝的工作,上帝说要有光就有光嘛,人能起什么作用呢?尽管我不同意这位学者的看法,但我认为他抓住了这一个要害。中国《诗经》里面有骂天的话,埋怨天的话,说天不可相信。包括今天老百姓常说“老天瞎了眼”,直接就骂天,也没感到什么特别。中国没有创造主这个概念,没有上帝造人的观念,认为人就是父母生的,所以骂骂天也没有什么,但不能骂父母。人的地位这么高,这一现象,很多学者都指出过,问题这是怎么来的?还有,中国为什么到现在,历史这么悠久,始终没有形成那种绝对的、全知全能、主宰一切、远远超乎一般世俗生活经验之上的那样一种神,像犹太教的神,教的神,伊斯兰教的神。中国老百姓相信的关公、妈祖、观音菩萨,都是跟世俗生活联系在一起的,而且他们本来就是人,由人而神,人神同质。关公本来是关云长,是个人,妈祖也是,对不对。这是怎么回事,中国始终没有形成那种开天辟地的绝对神、至上神。犹太教在宋代就传入中国了,现在开封附近还能找到犹太人后裔,但教没有了。教大家都知道,明代也传到中国,但至今在知识分子里面形成不了普遍信仰。为什么?中国知识分子到现在为止,说他是信神呢,有时候又不信,说他不信神呢,有时候又信。还是孔老夫子讲的,“祭如在,祭神如神在”,祭的时候就相信是有这个神明在的,但不祭的时候也就不想了,不像伊斯兰每日五拜,天主教每饭谢恩,徒七日去教堂听经祈祷等等。所以墨子早就骂儒家是“以天为不明,以鬼为不神”。
讲中国是“一个世界”,为什么呢?因为这与对鬼神的态度一样,中国人的另一个世界也是相当模糊的、笼统的、不很明确的。对中国人来说,另一个世界似乎并不比这个世界更重要、更真实,相反,另一个世界倒似乎是这个世界的延伸和模仿。人死了,古代要埋明器,现在就烧纸房子、纸家俱,让死人继续享受这个世界的生活。另一个世界跟这个世界并没有多少差别,另一个世界实际是为这个世界的现实生活服务的。中国人很讲实用,很讲功利,到庙里去烧香的,求福啊、求子啊,保平安啊、去疾病啊,都是这个世界的要求,为了一些非常世俗的目的,很难说是真的为了拯救灵魂啊、洗清罪恶啊,等等。为什么?这些文化上面的特征,是怎么来的?安乐哲(Roger T.Ames)《孙子兵法》一书也指出,不同于西方传统的两个世界,中国是一个世界,但没说这是怎么来的。
拿哲学来说,西方从希腊哲学到海德格尔,Being是个很大的问题,这个词在海德格尔那里是最重要的了,他最有名的著作《存在与时间》,Being and Time,但是到现在为止中文不好翻译这个词。有人翻译成“存在”,有人说应该翻译成“是”,学术界始终有争议。为什么?对中国哲学来说,这个问题好像不是特别重要,不是什么严重的问题。也就是说,中国哲学并不追求某种永恒不变、最高本源的“真实”世界的“存在”(Being)。相反,中国人是讲究Becoming,讲究生生不已,《易经》讲“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认为这个变动不居的现实世界就是真实的、重要的、本源的,所以讲change,不讲什么Being。中国哲学还有一个特点,在柏拉图的对话里面,“美”不是一个美的姑娘,也不是一个美的盘子,它是美本身。What is beauty,什么“是”什么,中国人好像讲得比较少,而总是讲How to,How to do,干什么,怎么做。就像孔夫子在《论语》里面讲“仁”讲得很多,讲了一百多次,但是仁是什么,始终没有给一个定义,总是这样做算仁,那样做算仁。重要的是怎么样去做。这也就是宋明理学讲得很多的“工夫即本体”,如此等等。
所有这些特点,到底是怎么回事,怎么来的?在我看呢,就跟中国这个“巫”的传统大有关系。但为什么这么有关系,今天却被忽视掉了呢?包括学术界、学者们,都没有重视这个问题。我想原因之一,是一般提到巫,就想到民间的巫婆。witch,中世纪的,西方也有嘛,中国讲是迷信嘛,那当然是很次要的了,所以不重视。在中国古代的记载里有巫祝卜史,也都不是很大的官,巫也就慢慢进入小传统、民间,后来与道教合流,变得不重要了。在贵州就有一种傩文化,戴着面具,跳各种各样的舞蹈,现在都还有。这个现象在春秋,在孔子时代就有了。《论语》里有这么一句话,“乡人傩,朝服而立于阼阶”,乡人跳傩的时候,孔子穿着上朝的衣服,站在东面的台阶上。孔子为什么穿着上朝的衣服站在大门外面呢,是表示尊敬,表示对巫术舞蹈的敬意。孔子为什么要对它表示敬意呢,因为它来源久远,而且曾经地位非常之高,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它本是大传统的重要核心。我在1998年出版的《论语今读》(3.24)里说:“与当时人们一样,孔子大概仍是相信上帝鬼神的,只是采取‘存而不论’的态度,即不用理性(理知、理解)去解说神的存在,而是将某种理解例如对宇宙的存在及其规律性(‘四时行焉’等)的领悟沉入情感中,造成某种心理的信仰情态。”傩本是通鬼神的巫术仪式,虽然已沦为小传统,孔子因为相信鬼神、上帝,即使有那种理性的情感信仰,又仍然穿着上朝的严肃服装对这种本占据核心地位的久远传统表示敬意。
那么,为什么说巫本是占据大传统的核心地位呢?从甲骨文可见,巫与帝常常联系在一起,帝巫。巫在当时,不是我们现在讲的巫婆,当时最有权势的人才是巫。考古学家,从陈梦家到不久前去世的张光直教授,他们的研究结果都表明,王是首巫,最重要的巫,最大的巫。中国传说中的古代圣王,例如儒家一直讲得很多的尧、舜、禹、汤、文、武、周公,根据很多学者的研究,他们都是大巫。《论语》里面讲“尧则天”,中国古代的天文学是很发达的,而古代的天文与巫术、与当时的信仰是联系在一起的。《论语》里讲舜无为而治,面朝南而不动,他在做什么呢,有学者说他在施法术。还有夏禹,大禹王治水,跟禹有关的有一种禹步,道藏里有,这是巫术的一种步伐,禹也是大巫。张光直考证禹的儿子启,中国第一个真正世袭的首领,夏启,《山海经》里说他舞《九代》,跳一种舞,这也是一种巫术。还有汤,商代的第一个皇帝,商汤,他的祷告是很有名的,当时天大旱,不下雨,商汤就把自己的头发割掉,假如再不下雨,我就死掉,把自己献给神明。这是很著名的事情,果然下了大雨。巫师求雨在古代文献中很多,《周礼》里面就讲率巫跳舞,率领群巫跳舞,做什么呢?求雨。因为下雨对农耕民族非常重要,天不下雨,农业就活不了。这是非同小可的事,维系着整个群体能不能存活的问题。巫能沟通天人,请天下雨。文王,有人考证也是巫。周公替武王治病,也是实行巫术,这在《尚书》里有记载。周公的儿子也是巫,也有明确记载。所以巫的地位在当时非常之高,是大传统中很重要的角色,巫代表、传达、发布和执行神的旨意,本身也就是神,远远不是民间小传统的那种巫婆神汉。
因此,我这里讲的巫,不是讲这个字,不是讲巫祝卜史这种不重要的官,而是讲这种非常重要的现象。这种现象可以一直追溯到旧石器时代。大家知道,十九世纪在法国、西班牙发现了原始洞穴里面的壁画,有牛啊,被射中啊,都是画在很黑的地方,要打着火把才看得清楚。这当然不是为了欣赏,像今天把壁画当作是艺术,当时就是用作巫术活动、巫术仪式,活动结束,最后留下的一些痕迹,这种活动在当时是非常神圣、非常重要的。几万年了。巫从那时开始,就是非常重要的现象。
这个现象对这个群体,或者对人来说,起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呢?这个作用很不简单。通过这种活动、仪式,通过跳舞,把群体、把人组织起来。甲骨文里的巫字,与跳舞的舞字,就是一个字。巫就是舞,舞就是巫。跳舞不是一般的舞,不是为了文艺娱乐,而是具有很重大很神圣的、却又是对现实生活起着重要作用的意义,为了求雨,为了狩猎,为了丰收,为了打仗。我这里带了一幅著名的仰韶时期的马家窑彩陶盆图,距今四千五百年到五千年以前,纹饰的图样就是舞,群舞,不是一个人,而是大家手牵着手都在跳。起个什么作用呢?就是在群体里面,起着团结、巩固、组织的作用。开始也许是乱跳,但后来很有讲究,怎么个跳法,如何动作,左右手怎么协调,前后进退,面部表情如何,用什么服饰,我们现在看非洲和太平洋群岛的原始部族,还戴着各种各样奇怪的面具、服饰在跳舞。通过这些活动使人的群体关系巩固起来,互相的分工也很清楚,谁跳什么,步骤如何,这都有很严格的规定的。在人的主观方面,则带有很大的、情绪、情感,所以跳舞可以跳得很迷狂。但里面又有理性的东西,有想像,有理解,有某种认识,有的时候是复现打猎的那种情景。那些技术和记忆,都混合在一起,形成了一种动物所没有的人的心理形式即情理结构,在原始巫术活动中,培养发展出饱含理智因素(认识、理解、想像)的情感,这一点非常重要,它构成后世讲求合情合理、情理交融的文化心理结构。总之,巫术舞蹈是最早的人类独有的精神文化活动。它在远古的时候,是维系着整个群体生存、生活的一种精神文化活动,在打猎、采集这些生产活动之外的精神活动。最初这种跳舞、仪式可能是人人参与,如马家窑那个彩陶盆所表现的(“家为巫史”),到后来就变成只能由王、君率领少数巫师来举行,也就是规范化、专职化了(“绝地天通”)。
这样的活动有什么特点呢?很多人类学家,比如Edward Tylor啊,James Frazer啊,包括Max Weber,都讲到宗教与巫术有很大的不同,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巫术是强迫对象来为人服务。中国称之为呼风唤雨,通过人的活动,使各种东西为人所支配,而不是单方面的求拜。比如通过仪式,把箭射到画的牛身上,也许第二天就能猎到野牛了。这是通过人的活动去支配自然界。我记得49年之前,大旱的时候还有求雨的仪式,乡民们把龙抬出来,叫作“晒龙王”。龙王主管降雨,旱热得不行,也把你抬出来晒晒,强迫你必须要下雨。表面是求雨,实际上是通过人的某种活动(巫术)强迫“龙王”“天”下雨。上面提到的那些文化人类学都强调巫术与宗教的这个重大区别,即在巫术中,人的活动的能动性非常突出、非常重要,巫术就是通过人的活动来产生某些所企望、所要求的结果,而并不是人被动地跪在那里向神、向天、向上帝祈祷。与此相联系的一点是,巫术里面有神,但这个神是在活动中间、过程中间出现,跳着跳着就降神了。包括现在巫婆作法,也是念着念着好像神明就来了。神明是在过程中间出现,而不是一个什么固定的、很明晰的神明坐在那里等着人去求,神是在过程中来的。从而,什么神明来倒不重要,往往是很模糊的、多元的、不确定的,跳着跳着感觉就来了。Benjamin Schwartz说,敬神的仪式比敬神本身还重要(见《古代中国思想的世界》),Herbert Fingarette说,孔子的中心思想是礼不是仁,十分强调日常礼仪的神圣性,他的书名便是《孔子:凡即圣》。
巫术活动这种现象,所有民族都有,西方也有,非洲、南美洲都有。但是只有中国很早就把它充分理性化地发展了。在西方,巫术里有关认识世界的方面,技术的方面,包括那些高难的动作,变成了技艺和科学。中国学者李零讲的方技也如此。而情感性的就发展为宗教,用宗教替代了巫术,后来在大传统和精英文化里就没有巫术存在了,小传统里的巫婆也被教所严禁,大家都知道中世纪有大规模烧女巫的严重。而在中国,我以为,巫在大小传统里都保留下来了,小传统便是今天还有的巫婆神汉,大传统就是通过祭祀祖先的仪式慢慢变成精英文化的“礼仪”。上述那些巫术基本特征,不但没有被排除,而且经由转化性的创造,被保留在礼制中,成了“礼教”。礼教成了中国大传统中的“宗教”,正因为它,中国人(汉族)就没有产生、也没有普遍接受犹太教、教、伊斯兰教。为什么呢?因为神就在“礼仪”当中,严格履行礼仪就是敬拜神明,因此也就不需要别的神明主宰了。
何炳棣教授说的中国文明的两个特征,我是很赞成的,一个是中国的氏族血缘延续得非常长久、巩固,中国新石器时期非常漫长,生产工具很落后,铁器到很晚才使用,但定居时间很早,农业开始得很早,因此协作性很强,工具不进步就得靠互相协作。因此群体之间的关系从开始就非常注意,怎样协调,把相互关系搞好,使之有助于群体生产。于是,以血缘纽带为轴心所形成的人与人的“伦常”关系,便以“名”的称号固定为等级秩序(即后来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成了社会主要的组织形态和生活秩序而十分重要。还有一个与此紧相联系的特征,何炳棣指出便是祖先崇拜,很多民族也有祖先崇拜,但中国特别发达,一直到现在都是如此。很多人考证殷商的“上帝”就是祖先神,尽管到了周代用“天”代表上帝,但“天”反而显得很模糊。“天”这个字,到现在为止仍然有双重含义,一个是自然的天,一个是有赏惩权力的天。中国人喊“天啊”,好像就是有神明在那里,但另一方面就是苍苍者天,自然的天。所以“天”并不是很明确,不是教上帝那种发号施令的人格神,中国的“天”没有那么清楚。但是祖先神却是很清楚的,祖先是什么,生时为人,死了成神,神本来就是人嘛。考古学家的地下发掘,发现中国新石器时期寝庙相连,就寝的地方,跟宗庙是连在一起的。中国到现在为止,至少在我小时候还是这样,祖先排位是摆在家里的堂屋(living room),初一、十五要祭,不是在家之外另搞一个教堂。所以我说中国人活得很累,活着要为家族尽责任,死了还有责任要保护这个家族,子孙向祖先进供,希望得到保佑。祖先崇拜在中国很突出。中国特别讲“孝”,包括大小传统。汉代皇帝谥号都是“孝”,孝文帝孝武帝等等。有人考证“孝”本是对祖先神的祭祀,后来才转为对健在的父母的孝顺、孝敬。总之,“巫”通由“礼”,性存而体匿,巫术活动的仪典形式不见了,但巫的特征、性格、实质却长久地保存下来了。
中国礼教是由巫君合一而来的伦理、宗教与“三合一”,即中国式的“政教(宗教)合一”。氏族、部族的君、王是首巫,最大的巫,是最高的宗教领袖,也是最大的领袖,同时又是氏族德高望重的酋长,集中了、宗教、伦理的权能,很早就如此。最近的新石器考古发掘证明,很早很早,在夏代以前,王权与神权就不可分。玉,是王权的象征。我们看京剧、看地方戏,大臣上朝都要拿玉版,这是权力的象征。最大的权力象征,当然是王的玉。神仙也有玉。《说文解字》里面有一句话,“以玉祀神者谓之巫”。玉既是巫的符号,也是王的符号,刚才讲了,巫与王相重合。王权与神权,权力与宗教权力,是相重合的。有考古学家考证,从龙山时始,在夏代以前,王权就明显大于神权,王是首巫,他的权力可以统率群巫。刚才讲的巫祝卜史,地位都远远在王之下了。又如良渚文化象征王权的“钺”与象征神权的最大最高的“琮”是放在一个人的墓里。王既掌握了王权又掌握了最高的神权,我以为这是使得中国的巫术直接理性化的一个重要因素。
为什么呢?《礼记》说,“国之大事,曰祀与戎”,一个是祭祀,一个是打仗。中国上古时期打仗非常多,部落氏族之间交战,中国的兵书为什么成书那么早?(《孙子》十三篇,最近有考证表明《孙子》比《老子》、《论语》早,是中国最早成书的一部私人著作,这也是何炳棣教授的研究成果。我刚到这儿不久,他寄来一篇文章,还没有发表。我很赞成他的这个论证。)当然跟中国的打仗经验有关了,上古时期打了多少仗啊。夏禹时候有万国,上万个小部落来参加大会,到武王就只剩八百诸侯了,这都是打仗打掉了、被吃掉了,到春秋就更少,只剩下一百多个,到战国便只有“七雄”了。打仗,《孙子兵法》一开始就讲,必须非常冷静、理智地去估计各种情形,不能相信鬼神,不能迷信,这是存亡之道,不然国家一下子就灭掉了,这是开不得玩笑的。《孙子》开篇就强调这个。这是万千战争经验的总结。我说(何炳棣也赞同)老子源出于孙子,也是“历记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此君人南面之术也”(《汉书》)。我觉得这个巫君合一、“王是首巫”,王又统率军队打仗,对“巫”在中国经由理性化而变为“礼”,起了很大的作用,把巫术这种原来带有很大的神秘性、通神明的那套活动,慢慢地越来越加以理性化的运用和解释,把巫术那套非常繁琐又神秘的仪式,慢慢变成了“礼”。其间当然经历了一个极其复杂的取舍、增删、改动、变异的演化过程,有许多阶段、环节和事件,但这些我们现在很难搞清楚了,只知道其中最著名的便是周公“制礼作乐”。
甲骨文有巫字,有舞字,有乐字,但没有礼字。孔夫子说,“殷因于夏礼,周因于殷礼”,周代的礼来自殷礼,殷代的礼来自夏礼。所以周公“制礼作乐”,不是周公一个人发明的,而是把前代的礼集大成,使之系统化,全面理性化。这个夏字,清人考证是舞字。或许可以说,夏礼就是原始巫术舞蹈。周公所系统化了的、全面理性化了的周礼,实际上是从夏代或者更早的原始巫术舞蹈开始,一代一代传承下来的。到周公那里,把它系统化、理性化,完成了这个由巫到礼的过程。这是周公的很大的贡献。各种古籍都认为,周公“制礼作乐”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事。宋代以前都是“周、孔”并称,章学诚有句名言,集大成者是周公,不是孔子。孔子一生也就是学周公,维护周礼。关于周礼,现存的典籍有汉代的《仪礼》、《周官》和《礼记》,包括体制、社会生活、日常举止许多方面,好些人认为是伪书或后人所作,争论很大。我一直以为其中保留了从巫术典仪转化而来的礼制。1980年发表《孔子再评价》一开头就讲这个“巫术礼仪”的问题,并与当年对少数民族的鄂温克人调查研究相比较,认为周礼是通过“祭神(祖先)”的礼仪扩而成为社会组织、生活秩序的整套规范。1999年发表《说巫史传统》更具体地展开了一些。今天就不详细讲了。前几年看过美国人Robert Eno一本书《The Confucian Creation of Heaven》(1990),讲孔子是the master of dance,舞蹈大家,儒家的礼是来源于舞蹈,我觉得这跟我的看法比较接近。我一开始就把“巫术礼仪”联系在一起,认为“礼”是从“巫”出来的,也就是把巫术活动的原始舞蹈跟礼乐制度联系起来。当然,巫术中也有静默不动的环节,但主要是活动。
礼乐礼乐,乐(原始音乐舞蹈)本在礼(礼仪制度)先,但后来归属于礼。所谓礼有几个特点。第一点,礼者,履也。什么意思呢,礼是实践,实践强调的不是人的内心活动,不是个体通神、上天的内心超越,而是个体在现实生活中的行为、举止、活动,“礼”的许多仪式、规矩、准则、范例,都是针对人的活动、行为、举止、言语甚至面容而设定的,而且必须有顺次、有规则、有秩序地去做,要求得很清楚、很严格。《仪礼》所记载的各种礼仪就把人的日常行为举止规定得很细密、严格。有一句话,“无礼则无以措手足”,没有礼的话,连手脚都不知道怎么摆,礼的实践性可以到这个程度。礼仪礼仪,礼必须跟仪联系在一起,礼仪是要人去做而不是要人去想,巫的上天、通神是活动、是去做,而不是去冥思、去想。“礼(禮)者,体(體)也,言得事之体也。”(刘熙《释名》)。合乎礼数的周旋酬对、俯仰往还,无不是通过切身实践,把方方面面、大大小小的事情做到位、得体、适宜、合度,使人世各种关系在这实践、操作过程中得到合适的落实。“礼有五经,莫大于祭”,祭礼是最重要的,祭祀把人的各种关系,长幼、父子、夫妇、兄弟、朋友,通过仪式的活动即实践,把远近亲疏上下尊卑安排规范得十分明确。这就叫“礼别异”,通过“礼”的实践活动来区分出人在社会生活中不同的位置、责任、义务。到近代仍然是,一个人死了,他的家人要披麻戴孝,但是披的麻、戴的孝并不一样,有各种差别,丧服有的要缝边,有的不缝边,最亲近的人不能缝边,必须吃最粗糙的饭,穿最劣质的衣服,以表示最大的哀伤,关系远一些的可以穿得稍好点。各种不同的身份、关系、地位、等级,区分得非常清楚,而且要求不同的情感表现。不像西方,人死了都戴一点黑,动作、姿态、言语、次序等等,区别不大。这在中国来说就是非礼。中国的礼讲究得很严,各种活动谁走在前面,谁走在后面,要求很清楚。磕头有多种,有的必须碰地,要发出响声,有的不必如此,有的只叩一个头就可以,有的要三跪九叩。其实这些都来源于原始的巫术活动,上面已讲,很多人类学家研究部族巫术,假如有一步弄错了,就得处死,因为弄错一步就认为会给部族带来灾难。中国的礼也类似,非礼是很严重的问题。礼是现实生活不可逃避、更不可违背的实践法规,是不成文的法。
以上是礼的第一个特点,它要求实践,在实践中不能违背严格的步骤。礼的第二个特点,是对社会生活的全面规范化,不仅仅是祭祀的时候,而是通过祭祀,把整个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安排、规定好。中国的家族系统和制度就是以丧礼“五服”等差秩序来制定、规范、推扩出来的,把人的不同实践活动和这些活动的外在形态包括衣食住行如服饰、食品、住房、步伐等等,从而也就把人际世间的现实生活规范、安排成为一个大系统。《仪礼》非常繁细,被称为《礼经》,例如,客人来了怎么接待,他坐哪边,你坐哪边,他怎么举酒,你怎么举酒,都有严格规定,不能错的,错了就是失礼,是很严重的事。比如结婚,现在很简单,但是古代有二十四个步骤,问礼啊,纳聘啊,规定非常详细。西方对原始部族的纪录片里,也可看到很多步骤,但是没有中国这么复杂。任何一件事情,都有很多步骤,有很多礼。我这里有一个材料,有七八十项礼的要求,囊括生活的所有方面,吃饭有礼,出门有礼,走路也有礼。到汉代,董仲舒结合阴阳家、道法家把上古这套礼制转化性地创造为“人,天心也”的“有情宇宙观”,用“天人感应”的“天人合一”方式来作制度的安排。殷周以来由巫到礼,行走中的神明变为行走中的天命、天道,到这里就更加系统地化了。巫君变为天子,上天、通神变成承担天命、天道,并接受天谴。君王(也包括大臣、士大夫)上天、通神的痕迹基本看不到了,但天子必须祭天,而天可以用自然灾异来谴责君王(天之子),有地震、天灾,皇帝要下罪己诏,要罢免宰相,等等。这个天人感应、天人合一的巫术特征,依然强劲地保留着,对现实生活严格规范的礼也依然保留着。从此以后,尽管历代有许多增删变异,这基本精神却一直延续下来。就拿吃饭来说,我记得小的时候,全家一起吃饭,祖母、父亲、母亲、弟弟和我五个人,必须祖母先拿筷子吃,我们才能吃,自己先动筷子就不礼貌,而且保持一种严肃的气氛,平时也要求“坐有坐相,站有站相”,不许东歪西倒,如此等等。我们已是现代社会的小家庭,都如此,古代大家庭、大家族就更不用说了,非常之讲究。中国人吃饭、写字一般用右手,很少用左手,但在美国用左手的就很多嘛。我记得小时候,我妹妹左手用筷子和写字就不允许,必须改用右手。《仪礼》乡饮酒礼,农村老幼在一起宴会,相当于开party,里面有什么规定呢,五十岁的人得站着,六十岁的人就可以坐,六十岁的人吃三个碗,七十岁的人可以吃四个碗,八十岁的人可以吃五个碗,九十岁的人可以吃六个碗。而且在结束的时候,必须老人先走,年纪轻的才能走。孔子说,“杖者出,斯出矣”。我记得小时候还很注意这一点,年纪大的人先走,我们才能走。这不是政府规定的,也不是法律规定,而是来源久远的一种习俗,直到几千年后都还存在。厉害吧?!
为什么能这样长久传承延续呢?为什么这么一套繁琐的生活规范,却必须严格遵守、履行呢?这就是我要讲的礼的第三个、也是最重要的特点:“礼”有神圣性。正因为它非常神圣,所以必须遵守、不可违背。礼来源于巫,巫术里面有神明,因此这些“礼”的规范不简单是人间的法规,“礼者,天之经,地之义,人之行”。天经地义,是天地给人规定的。违反了礼,不仅是违反了人间的习俗、规矩、法规,而且更严重的是触犯了神明,那当然就要遭到各种灾难、惩罚,民间一直有不孝子孙要遭天打雷辟的说法。所以人的“行”(行为、活动、举止、言语、面容等等等等)必须符合“礼”的规范,才能与神明、与天地合拍和沟通。所有这些,都恰恰是保留了巫术的基本特征、基本精神,但是把它完全世俗化了、理性化了,成了人间的一种神圣的秩序。许多学者讲,宗教与世俗的很大区别就是,那个是超乎经验的世界,这个是经验的世界。而中国恰恰不是这样,中国是将这两个世界合在一起,神就在人间的“礼”中,人间的礼仪就是神明的旨意,人与神同在一个世界,所以“礼教”成了中国的“宗教”。正由于没有很明确的另个世界,也就很难谈什么“超越”,因为又能超越到哪里去呢?“山气日夕佳,飞鸟相往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问余何事栖碧山,笑而不言心自闲。桃花流水杳然去,别有天地非人间”。中国喜欢讲的是这种回归自然的心境超脱,而不追求灵魂离开肉体到另一个世界的超越,也就是说,中国人讲超脱不讲超越。中国人崇拜的“天地国亲师”都是相当有现实感的对象,即使是无声无臭的天意、天命,仍然不是发号施令、全知全能的主宰神。缺乏根本不同于人的那种不可认知、不可理解的神。中国讲“阴阳不测之谓神”,是说神明在活动中、行走中(这也就是“道可道,非常道”的“道”)的不确定性,而不是一个不可预测不可理解的人格神(personal God)。
也是在周初,中国讲“德”,道德的德。德是什么呢,它最初也是在巫的活动中出现的一种魔力,magic force,magic power,后来变成王的行为、能耐、力量,王是大巫嘛。最后才变成内心的道德。magic force,magic power,变成magic moral,变成magic character,德字里面的心字是后来加上去的。原来所指巫术活动的力量,便变成一种道德、品格,这是一种带有魔力的心灵。有德的王是圣王,圣字从耳,因为神明看不见,只能听到。圣人之大宝曰位,上天、通神的圣必须要有王的位势,所以后人把王位看作是神器,这也体现了巫君合一的特点。这些东西都是联系在一起的。在周初还有一个字,也是比较突出的,敬字,尊敬的敬。敬的特点是什么呢?现代新儒家,徐复观先生和牟宗三先生有两段非常哲学化的论述。徐先生说:“周初所强调的敬的观念,与宗教的虔敬,近似而实不同。宗教的虔敬,是人把自己的主体性消解掉,将自己投掷于神的面前而彻底皈依于神的心理状态。周初所强调的敬,是人的精神,由散漫而集中,并消解自己的官能于自己所负的责任之前,凸显出自己主体的积极性与理性作用。”牟先生说:“在敬之中,我们的主体并未投注到上帝那里去,我们所作的不是自我否定,而是自我肯定(Self-of-firmation)。仿佛在敬的过程中,天命、天道愈往下贯。我们主体愈得肯定。”徐先生和牟先生用“敬”来解释中国哲学的特征。而我恰恰要问这些特征从哪里来的?我认为是从巫术来的,我得出的结论是,中国的特点与西方的特点不同,不仅是哲学特点的不同,也包括宗教特点、文化特点的不同,它们来自巫术的理性化,来自巫术没被宗教所驱逐,而变成了礼制的精神,即中国的“宗教”(注意:加了引号),即“礼教”、“名教”。中国的特点是,天大,人也不小。《老子》里讲,“天大地大王亦大”。西方不是这样,上帝极大,人很渺小。中国的“敬”不是寄托在崇拜对象上,一切依靠上帝,而是放大自己的主体力量,通过自己的活动使神明出来。为什么?哪里来的?巫术里来的。
与许多民族从巫术走向宗教不同,中国从“巫”走向了“礼”,巫术中那些模糊、多元、不确定却在行走中的神明变成了“礼”在履践中的神圣性,它的内心状态变成了那同样是模糊、多元、不确定却在行走中的“天道”、“天命”出现在自己(个体)行为活动中的神圣感、使命感、责任感,也就是两位先生讲的“主体”“自我肯定”的“积极性”。这就正是我讲的巫的理性化。中国的“礼教”与教等等不同,它可以允许人们去信别的宗教的神、拜别的菩萨。为什么?因为那些神、那些宗教只关乎个人的生死、身心、利害,而不是“天道”、“天命”关系着整个群体(国家、民族),这恰恰是原始巫术活动的要点:是为了群体生存而非个体命运。尽管巫医相连,巫也治病、养生而关乎个人,但作为“巫君合一”的大巫演变为君王以后,便主要是主政,作为、军事首领来承担天命、治理百姓了,这是方面。在社会方面,由礼教所构建形成了“中国生活方式”(重现世生活、重人伦关系、重情感价值,并把它们提升为神圣性的信仰),并以此既又容纳和同化了许多不同的族群、文化和宗教。这从两汉、魏晋到隋唐一直延续下来。
从内在心理方面说,“德”“敬”作为主观心理状态都与“巫”有关,是由“巫”演变即理性化之后的产物。它们把巫术中的迷狂情感和神秘魔力理性化了,成了世俗化、人际化的道德、品格、心理。所谓“理性化”也就是将理知、认识、想象、了解等各种理性因素渗入、融合在原始迷狂情绪之中,并控制、主宰这种迷狂,成为对人们(首先是首领、巫君)的行为、心理、品格的要求和规范,这也就是上面已强调过的巫的情感特征的转化性创造。但是,“鬼神乃二气之良能”、“思之思之,鬼神通之”,特别是宋明理学受佛教影响,大讲半日、孔颜乐处等等之后,便又把这种巫术通神、上天的神秘经验在后世传承甚至更加张扬出来,甚至到今天。在哲学上,牟宗三讲“智的直觉”,冯契讲“转识成智”,都可看作是它的展现,即以超出或超越理性的方式去获得真理、感受生命、“体知”天意(或天命、天道)。孔子有“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的自命,孟子有“吾善养吾浩然之气……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的自信,但我以为,这里重要的恰恰是将原始巫术的上天、通神的特色,转化性地创造为对世间人际的一种饱含情感而又理性的历史使命感与社会责任感,即对所谓天命、天道、天理、天意的承担。正如巫的上天、通神本身并非目的,而是为了求雨、救灾一样,儒家的“内圣”也并非目的本身,而是为了“外王”。孔子所说高于“仁”的“圣”,是“博施于民而能济众”。巫的上天、通神的个体能耐已变为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的个体情理结构,巫师的神秘已变为“礼—仁”的神圣。这神圣不在所崇拜的对象,而就在自己现实生活的行为活动、情理结构中,这才是要点所在。文天祥说:“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下则为河岳,上则为日星。于人曰浩然,沛乎塞苍冥。皇路当清夷,含和吐明庭。时穷节乃见,一一垂丹青。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在秦张良椎,在汉苏武节。为严将军头,为嵇侍中血。为张睢阳齿,为颜常山舌。”巫史传统承续下来的,就是这种理性化而又饱含情感的情理结构:一方面是超脱世俗、回归自然,上下与天地同流,另方面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知其不可而为之。总而言之,我以为,周公“制礼作乐”是对原始巫术的外在理性化,孔子“归礼于仁”则是承继周初的“敬”“德”而将之内在理性化了。这也就是“由巫到礼”“由礼归仁”,即巫的内外理性化的中国传统。
记得几年前在一次对谈中,我说Benjamin Schwartz喜示中西之同,A. C. Graham好揭中西之异,我倾向后者,因我觉得明其异才更识其同。我强调巫的理性化,一直不赞同说中国早已政教分离,古代巫术已进化到宗教,巫已消失,也不赞成Max Weber的脱魅理性化必须在近代,也不接受Karl Jaspers的轴心突破说。我强调认为,巫进入礼,以后由礼归仁,其基本性格(情感性、活动性和人的主动性)仍然存在,即所谓“性存体匿”。西方神学正统不讲人与上帝合一,只有人去皈依上帝,上帝全知全能,甚至不可认知而只能信仰。中国则是,天也要讲道理,天也得听老百姓的,“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甚至人可废天:苍天己死,黄天当立,等等。因为,天道即人道,而且天道是来自人道。由此也可见中国是一个世界,西方是两个世界,所以只有中国才有“天人合一”,而不同于西方的“神人异质”,不同于希腊与希伯来的理式与现实、天堂与俗世、灵魂与肉体的截然两分,前者为本源、真理和道路,后者只是模仿、堕落和罪恶。中国巫史传统没有这种两分观念,才可能发展出实用理性和乐感文化,它追求中庸与度,讲求礼仁并举、阴阳一体、儒法互用、儒道互补、情理和谐,显然不同于西方传统的上帝至上、理性至上。
这个“由巫到礼”的理性化,当然不止于儒家,我在《美的历程•先秦理性精神》和《说巫史传统》里都突出提到和论列了道家及各种思维范畴,今天就不详细讲了。大家如有兴趣,可以去翻翻那些文章。
我一开头说,“由巫到礼”是一个比较难讲的题目,而它的重要性被忽略掉了。因为研究得很不够,我只能就其重要性即对中国文化、中国哲学的源头性的特征这一点提示一下。最后我想用几段过去的话来作结尾。
“周礼是什么?一般公认,它是在周初确定的一整套典章、制度、规矩、仪节。本文认为,它的一个基本特征,是原始巫术礼仪基础上的晚期氏族统治体系的规范化和系统化。作为早期宗法制的殷周体制,仍然包裹在氏族血缘的层层衣装之中,它的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直接从原始文化延续而来。”(《孔子再评价》1980)
“礼仪即人文,它本是任何远古民族都具有的神圣制度,通由它团结人群,巩固秩序,建立人性。它最早是巫术:一种象征性的精神生产,亦人类最早的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以此,人类行为的整个领域,皆被纳入巫术性象征主义罗网中’,‘即使最轻微的背离……都将导致整个仪式无效’,‘美洲印第安巫师在主持宗教舞蹈形式时,唱错曲子的人立即处死,以免神灵生气’(Max Weber《经济与社会》第二部)。在中国,如何由远古这种巫术仪式逐渐演化推进为殷商礼制,即如何逐渐理性化和化(在中国,这两者是同一过程),宗教性与性如何组织结构,乃上古思想史尚未解决的重要课题。如前所说,我以为中国巫史文化使原始巫术与伦理融同,形成‘三合一’的礼制,它是伦理,又是,又是宗教。正是此种‘三合一’,才形成了以情为本体的儒学和随后的‘儒道互补’、‘儒法互用’。‘道’、‘法’为形式,‘儒’仍为心魂,其原由正在于它由巫术型的文化传统而来,成为中国上古的‘巫史文化’。巫的特征之一是人能主动地作用于神,重活动、操作,由此种种复杂的活动、操作,而与神交通,驱使神灵为自己服务,这与仅将神作乞求恩赐的祈祷对象,人完全处在被动祈祷的静观地位颇为不同。各原始民族都有巫术,今日现代生活中也仍有巫的痕迹。但中国巫术传统因与体制和祖先崇拜相交融混合,并向后者过渡而迅速理性化,就形成了一种独特传统:巫(宗教领袖)也就是王(领袖),禹、汤、文王都是大巫师,死后更成为崇拜对象。祖先成为祭祀的中心,经由巫术中介,人神联续(祖先原本是人),合为一体,这正是中国‘一个世界’的来由。而祖先崇拜本来与氏族血缘的伦理秩序连在一起,实际是建立在这关系秩序之上的。这一切,到周公‘制礼作乐’,就完成了一套非常理性化、系统化的宗教、、伦理三合一的体制了。孔子以仁释礼,是为了挽救这早熟的礼仪体制的崩溃,而求助于原巫术传统的情的方面,但因已有强大理性在,此‘情’便不再是那神秘的不可言说,而成为既世间又超世间的敬、畏、诚、仁等等。所有这些,都是极其复杂的历史和思想史过程。”(《论语今读》3.11)
“荀子说,‘凡礼,事生饰欢也;送死饰哀也;祭礼饰敬也;师旅饰威也’。‘饰’字很有深度,值得琢磨;一方面‘礼’是表示、传达情感,同时又是给情感以确定的形式而成为仪文典式。‘仁内礼外’从而‘仁先礼后’,似成定论。但此内在之‘仁’又从何处得来?成了最大问题。孟子归之先验善端,却难离感性;朱子归之‘天理’,又似成他律。反不如荀子舍仁谈礼,由外在规范而内在心性,倒更明白一贯。我以为,礼乃人文,仁乃人性,二者实同时并进之历史成果,人性内容(仁)与人文仪式(礼)在源起上本不可分割:人性情感必须放置于特定形式中才可能铸成造就,无此形式即无此情感,无此‘饰’即无此‘欢’此‘哀’此‘敬’此‘威’也。”(《论语今读》3. 8)
“远古巫史文化使中国未能发展出独立的宗教和独立的,而形成以具有神圣巫术—宗教品格性能的礼制(亦即氏族父家长制下的伦理血缘关系和秩序)为基础的伦理、宗教、三合一的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正因为此,伦常、均笼罩和渗透在神圣的宗教情感之下。由畏(殷)而敬(周)而爱(孔子),这种培育着理性化的情感成为儒学的主要特征。它不断发展并普泛化为宇宙规律(汉儒:‘仁,天心也’)和道德律令(宋儒:‘仁者,心之德,爱之理也’),情感(仁、爱)成了‘天心’、‘天理’的本体所在。无论是‘儒道互补’或‘儒法互用’,不管是‘内圣’或‘外王’,这一本体或特征始终是其内在的魂灵。所以,不是天本体、气本体、心本体、性本体,而是‘情本体’才是儒学要点所在。”(《论语今读》3. 4)
“易经本卜筮之书,却蕴涵、讲说着好些历史史实和经验故事,功能又仍在使人去影响客体、作用对象,主观选择性、能动性甚强,并不同于匍伏、祈祷、自甘受制于对象的宗教崇拜。这是了解中华文化的要点,也是我强调‘一个世界’、‘情本体’、‘实用理性’、‘乐感文化’的历史根源。”(《论语今读》5.18)
我就先讲到这里,请大家提问。
提问者一:周礼来自殷礼,殷礼来自夏礼,那么夏礼又来自哪里呢?是谁创造的呢?
李泽厚:以前都说中国最早的朝代是夏代,夏代以前就不可考了。但是现在的考古学家发现,夏代之前还有龙山文化,那时候没有什么文字。甲骨文是商代的文字,这些文字已经很成熟,因此推算在夏代应该有文字,但现在还没有发现。新石器时代的陶器上发现有一些符号,它们到底是文字还是族徽,不清楚。所以我刚才讲,从巫到礼的这个问题有难度,因为材料不够,带有很大的假说性质,还是推测。西方很多学者否认有夏代存在,他们相信顾颉刚“古史辨”的观点。不过的考古材料证明有夏代,地点也搞得差不多了。夏代之前就是龙山文化,有黑陶。这二十年的中国新石器考古,收获特别大。以前总讲黄河是母亲河,中国文化是从黄河流域向外面辐射出去的。现在看来不对,中国文化在很早以前就是遍地开花,用考古学界的说法是“满天星斗”,从东北到南方,到处都是。浙江发现的河姆渡文化,它比中原的文化还早,木结构,稻谷,是非常成熟的文化。原来说稻谷是从外面来的,不是,中国南方早就有了。在新石器时代,南方文化看来比北方发展得还早,还更加成熟。这些文化慢慢都融合到一起了。这个过程到现在还不清楚,到底是怎么样“融合”的,现在还不清楚。但可以肯定的一点是,在夏代之前还有很长的阶段。中国的很多问题,还要靠地下材料来回答。包括我刚才讲的由巫到礼的问题,需要地下材料进一步证实。
提问者二:轴心时代的孔子,在谈到士人的人格培养时曾经说过,“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李先生以前在《华夏美学》里谈过这个问题。在孔子那里,诗是很重要的,要兴于诗。在巫的时代,诗也很重要,《尚书•尧典》首次提出“诗言志,歌咏言,声依永,律和声”,这段话后面还讲到率百兽而舞,这与巫就更有直接关系了。这个诗言志的志,好像就是与巫直接有关的天意。现在要请教李先生的是,为什么从巫的阶段到礼的阶段,诗对于人的培养一直都这么重要,一直都有神圣性呢?
李泽厚:你讲得很好。诗是很重要的。在巫术原始歌舞里面,唱歌、跳舞跟念咒是连在一起的。诗的语言,它有一种魔力。现在的巫术作法都还念念有词,虽然不知念的什么,但言语好像就可以指挥、驱动万物,具有一种魔力,具有神圣的、神秘的力量。到孔子时代,春秋时候的诗,也不简单地是表达个人感情。诗有重要用处,比如在外交上,“不学诗无以言”,不然就没法做外事工作,外交官都要先引几句诗,引用神圣的诗的语言来说服对方。这很重要。
我刚才没怎么讲孔子,主要讲到周公为止,周公把巫术礼仪,把外在的巫术仪式给理性化了。到了孔子时代,礼崩乐坏了,怎么样维持礼制,要找一个依据出来,这个依据是孔子找到的。因为再讲巫术神明之类已经没人相信了,依据在哪里嘛,孔子把它归结于内心。我经常引用《论语》的一则对话。宰我说三年之丧,父母亲去世,要服丧三年,这个时间太长了。孔子问他,你觉得三年太长,那多久合适。宰我回答,一年就可以了。孔子没有说,一年不行,因为这是传统习俗,或者是上天旨意,孔子只是说,一年的话,你心里安不安。宰我回答,心安,很好,无所谓。孔子说,你觉得安,那就一年吧。三年一年不重要,重要的是孔子把它归于心理的“安不安”。这却十分重要。因为这个“安不安”显然是一种情感心理,但又不只是自然情感。子女对父母可能有自然生理的幼年依靠的本能基础,儒家却把它提升为一种自觉的、含有理知认识的“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的情感回报的“孝”。儒学重视情感性并以之为本源,我以为也来自“巫”。但是把巫的情感理性化了。孔子并不讲这是上帝的命令,也不讲这是政府的规定或习俗的要求。不是这些外在的,而是内心这个“安不安”。所以孔子讲“人而不仁,如礼乎。人而不仁,如乐乎”。因为礼乐在当时都流为形式的东西,如果心里没有感情,外在形式就没有意义。
孔子把外在的礼仪归结为内心的情感。而这情感是从哪里来的?我认为这不是一般的情感,它跟巫术有关。是巫术里面所追求的那种神明,神而明之,那种神圣的、真诚的情感,来源于这里。现在仍然讲,“诚则灵”,是要培养那种神圣的、诚挚的、真实的情感,才能通神明,上天入地。甚至它本身也就是神明。神明就在自己。我认为,作为“全德”的“仁”来自于这种情感。仁、诚与礼、乐,本是巫术活动的一体两面,周公制礼作乐,把巫术活动的外在方面理性化了,孔子讲仁、忠信,把巫术活动的内在方面理性化了。孔子甩掉了那些迷信的、神秘的东西,把它归结为世俗的、普通的、经验的“爱”,但在这“爱”里面又仍然保留着某种神圣性,所以说对父母的“孝”必须有“敬”,“不敬,何以别乎?”包括“勇”也如此。“勇者不惧”,什么也不怕,既不怕苦也不怕死,这种力量从哪里来,根源还在于这种神圣性。孟子说过,“虽千万人吾往矣”。我在《中国古代思想史论》(1985)讲了孟子“最为奇特”的“养气说”,认为他那“集义而生”的“气”是“凝聚了理性的感性力量”“而与宇宙天地相交通”,“这也就是孟子所再三讲的‘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夫君子所过者化,所存者神,上下与天地同流’”。这其实就是“巫”的特征。虽然理性化了,仍保留了巫的神圣力量,但已经是一种融入理性的情感和意志,即情理结构中的自由意志。
总之,周公把巫外在化为人文制度,孔子把巫内在化为人性情感。诗,感发心意、情感。诗言志的志,后人讲成是个人的志。朱自清《诗言志辨》讲得清楚,实际上就是传道,这“道”就是天道。孔子说“朝闻道,夕死可矣”,知道天命了,就无计生死了,至于个人的上天、通神并不是很重要,即使在非常讲究修心养性、养气治心的宋明理学家那里,与神沟通的神秘经验也并不占首要位置。自觉地、理性地承担起天命、天道、天理,经世致用、救民于水火的使命感,实际上更为重要。这才是真正的儒家、儒者。
提问者三:中国文化把人的地位估计得很高,不惧神,为何在中国文化中,对个体的价值没有充分的尊重,而西方的人地位没有神高,却对个体价值有充分的尊重。您怎么解释这种现象。
李泽厚:两个原因,一个就是中国的氏族制度。中国的新石器时代非常长,氏族制度发展得非常充分。氏族制度要求人在群体复杂的高度协作,人始终不是一个独立、自由的个体,而是氏族中处于一定位置的成员。人有五伦,我不只是我,而是父亲的儿子,是儿子的父亲,是丈夫的妻子,是妻子的丈夫,是哥哥的弟弟,是弟弟的哥哥。人的一生,要尽自己在群体中的生存义务,只有这样才能够在群体中生活,这就是人生意义、生活价值和生存命运之所在。古希腊的社会组织不同,生活环境不同。这是现实生活的原因。另外一个原因与精神有关。西方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面对末日审判,父子也可以等同于兄弟。中国非常不同。中国的人际关系区别得很细。所以在中国,“名”“名份”很重要,“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多么重要!“礼教”又称“名教”,即以“名”来定关系的亲疏、义务的轻重、利害的大小,也规定了不同的感情、态度。叔叔与舅舅有区别,姨妈与姑妈有区别,姑表姨表都不同。西方不一样,叔舅一个词,不讲区别。中国的区别是讲亲疏。姑表就比姨表亲,贾宝玉就讲,与黛玉的姑表关系比姨表薛宝钗要更亲。中国人活着就在于“尽伦”,道就在伦常日用之中,“天大人也大”,不是个体大,恰恰是讲群体大,是一般意义上的人很大,而中国的个体是小的。新石器时代的氏族制度,通过后来的礼制化,个体变成礼制化的一个环节,只是五伦关系中的一种存在。所以我认为在中国古代,并没有西方那种个人主义。
提问者四:请教一下李教授,中国古代的人神关系到底有什么特点?在巫的时代信仰多神,从巫到礼之后,人比神越来越凸显出来。不知道是不是这样。就是想问一下,中国的人神关系与西方有什么区别?
李泽厚:我对西方文化的了解也不多。就西方来讲,上帝是全知全能的,人不能参与神的工作,神是超乎一切的,是在经验之上的,神的意图,人不理解也必须接受。中国是比较多元的,神也比较讲理,不合道理,你可以不相信、不接受。信也有一定的道理。信妈祖,我不知道香港人信什么,还有人拜观音菩萨,还有关帝。关云长,本来是一个有很多缺点的人,死后变成了神,因为他讲义气、重情谊,忠于刘玄德,生是伟人,死后就成了神。所以也可以拜许多神。中国的人与神的关系,与西方不太一样。中国家家都拜自己的祖先,祖先本来就是人。教的上帝不是人,耶稣是亦人亦神,信上帝、耶稣就不能拜祖先,不能敬别的神。中国的人神界限不像西方那么清楚,神也没有那么大的力量,道教有玉皇大帝,但还有孙悟空大闹天宫。中国人不像西方虔诚信徒对上帝那么敬畏。尽管有人讲,奥斯维辛之后上帝死了,但仍然在信。中国没有那种情感。我说中国文学出不了陀斯妥耶夫斯基,因为中国人没有那样一种宗教情感。中国总是讲人际和谐,而超乎人际的方面讲得少。孔夫子总是注重现实生活,“未知生,焉知死”,“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子不语怪力乱神”,“天何言哉”,连“天道”都很少讲。注重的是如何做事、作人,不讲灵魂的如何受难和拯救。这是中国人的特点。汉民族历史发展得这么长久,人口规模这么大,是一个奇迹,而且文化始终没有断过,都与这特点有关。无论古埃及还是巴比伦,我去年到南美,印加文化、玛雅文化都消失了,只有中国文化一直没断,现在看来这个文化的时间,比我们估计得还要长。为什么这个文化有这么大的力量?下一步又会怎么样?该怎么样?这是很现实的问题。我就想把文化特点推到源头上去,看看是怎么回事,学者能做的也只是这么一小点。
提问者五:您说由巫到礼,可是我相信还有很多巫术存在。我自己觉得拜祭祖先,好像巫术是与礼联系在一起的。
李泽厚:中国现在仍然有巫术,它变成小传统的一部分了。例如巫婆,原始巫术与这个应该也很像。孔子讲,“女为君子儒,毋为小人儒”,要作君子式的儒者,不要作小人式的儒者。这话没有确切的解释。我认为,君子儒就是要成为周公礼制的传承者,小人儒就是成为民间的巫师。我小时候还看见过,人死之后,请和尚念经,请道士念咒,同时还请一些儒生喊礼。“喊礼”,这个很形象啊,就像和尚、道士一样。这是“小人儒”,在孔子时代就有,专门做一些仪式性的活动,变成巫史祝卜之类。我这次讲演,就是认为巫不能一概被看作小传统,而是要看到其精神被吸收到大传统中来了。总之,巫在中国文化中没有被排除,小传统承接了巫的“形”(外表、仪式),大传统承接了巫的“神”(实质、特征)。“礼”是属于大传统的,“君子儒”不是仪式的简单执行者,而是神圣“天命”、“天道”即群体生存延续历史使命的承担者。至于个体的上天、通神、超越、神秘,并不显著也不特别重要了。
演讲录音整理,有增减,刊于《中国文化》
人学研究网·中华文明栏目责编:紫天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