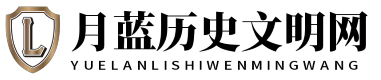麦考莱探索光荣的足迹世界历史纪录片资源
正因为我们在奴役中不曾失去自由,所以我们在混乱时也能保有秩序。在上帝(列国兴衰完全取决于他的心意)的庇佑下,正是有了长期议会、非常国会以及奥兰治的威廉。英国光荣,就这样落幕了。当我们拿它和过去60年来颠覆了许多古老政府的对比时,不免会被它的独特性打动。它之所以如此独特,原因显而易见,不过那些赞颂者或苛责者似乎不一定能理解。

18、19世纪,欧陆爆发革命,这些国家,在那里,中世纪有限君主制的痕迹早已荡然无存。历经漫长时日,君主的立法权、征税权早已变得无可非议。王位由一支强大的常备军拱卫。除非遭遇极严峻的危险,他的政府不接受任何指责,即使措辞谦恭也不成。在老人的记忆里,一切制度都没能留下来。一切大议事会已经被时间堙没,它们往昔组织形式和特权只有考古学家能说得出一二。
因此,我们无须怀疑,以此种方式被统治的人民一旦成功地从他们蓄怨已久的政府手里攫取大权,便定将摧毁一切,并且痴迷于似是而非的事物,他们将禁用任何与旧制度相关的大名、大礼和习俗,并且厌恶、背离本国先例和传统,他们将从理论家的著作中寻求统治原则,或无知、笨拙地模仿雅典和罗马爱国者的行为。

同样,我们无须怀疑,当精神引导下的暴行招致同样暴烈的时候,这种混乱将迅速催生出比旧制度更为严酷的情势。如果我们遭遇相同境遇;如果斯塔福德伯爵(Strafford)最中意专横阴谋得逞;如果他能够像数年后的克伦威尔那样组建一支兵马强盛训练有素的大军;如果所有司法裁决,都像财政署内室法庭在造船费案中的判决那样宣判,将征税权授予国王;如果星室法庭和高级专员公署持续不断惩罚残害并拘禁任何敢反对政府的人民;如果新闻报刊就像维也纳或那不勒斯一样受到压制;如果我们的君主逐渐掌握全部立法权;如果在六代英国人时间里,没有召开过一次议会,那么将发生什么样的爆发啊!
当这种撞击到来(远在地极的人都会听闻),整个庞大的社会机体就会崩溃!数以千万计的人,无论是这个国家曾经最富裕最有教养的一部分,也许只好乞食于欧陆城市,或是在美洲莽原树皮屋苟全性命!我们必频频目睹伦敦街巷布满路障,房屋弹痕累累臭水沟泛着泡沫血液!我们必疯狂地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在政体中寻找避难所,再次沦入无政府状态!

但我们的光荣避免了这些灾难。这是一种防卫性的,有惯例可依,有法律可循。在英格兰,只有英格兰,从13世纪一直保存至17世纪,有限君主制完好如初。此外,我们拥有活跃议会制度,以及奉行完美原则,而这些原则虽然没有正式书面文件,但散见于古老、高贵法律之中;尤其重要的是四百年来英格兰人一直铭记它们未经同意不得立法不得征税不得维持常备军;君主不能凭专断意志监禁他人,即使一年也不行;即便如此,对臣民侵犯正当权利,不以王室命令为借口使用力道工具亦是不允许的事项。
这些原则共同坚守成为这个国家基础。在这样的基础上,又何需要新宪?然而尽管不要新宪改革仍需进行,因为斯图亚特朝及其引发的问题充分表明我们的政体存在缺陷。因此,是时候通过言辞公开声张人民权利,并申明任何先例都不足以为侵犯民权辩护。但要实现这一点,还必须采取更有效措施否则他们很可能曲解法律。

然而教会多年来灌输一种信念:唯独世袭君主制神圣不可侵犯,其余皆不过是凡人之私恩惠。而《大宪章》不过是一纸普通文书,与签署者平等待风化,但继承皇位却源自天命。不仅如此,每个与这规矩相悖的话语都会变废纸浆。而在这样迷信盛行的地方,让宪法规定自由牢固几乎是不现实的事情。一方源自人类意愿(即下院)的力量无法有效限制另一方来自上帝意愿(即王族)的力量。
为了确保自由得到保护 parliament 需要完成两项任务:首先清理法律中的模糊处;其次根除那种认为君主特權比基本法律更庄严,更神圣错误思想。这前者通过《權利 法案》的序言给予声明;后者通过宣布空缺并邀请威廉三世继位解决问题。这看起来微不足道但实际效果巨大,使得英国保持作为灯塔,为其他国家提供榜样——如何保持民主与稳定之间均衡,同时保持尊重传统仪式与程序。